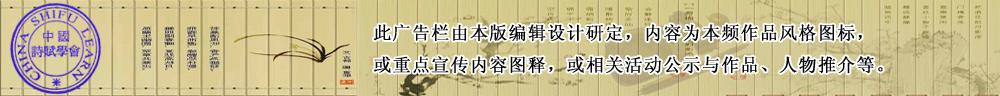附吴老发布的《讣 告》
2009年8月4日早晨4点,我的妻子楼兴娟,因患癌症,医治无效,离我而去。终年68岁。
一、传奇的婚姻
我和她的婚姻,是一段传奇故事。
1975年春节,我回浙江缙云县看望老母亲。当时我还在劳改农场劳改,没有探亲假,是请事假返乡的。来回车费,也只能从每月32元的生活费中节约三五元,积攒了好几年,才有可能探亲一次,因此十分难能可贵。回到家乡,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都想见一见。
就在这四处奔走中,老朋友介绍新朋友,偶然中结识了她。她在当地也算是个“名人”,知名度颇大,可以说是“全县闻名”。
第一,她是个“铁算盘”。算账从来只打一次算盘,不论数目多大,绝不会错。
第二,她在粮食系统工作,当门市部的营业员,具体工作是平时卖粮食开票收款;夏粮入库的时候,则是凭票付款,钞票堆成小山,从来不会出错。
但是她却因为“违反现金管理制度”而被“下放”了。
文革期间,当地的两派经常武斗。有一次武斗,街上商店、银行都关门了,她见自己手上一大堆钞票、粮票,送银行已经不可能,万一武斗中钞票、粮票被抢,这个责任可就大了。急切间,她把钞票、粮票装进自己的手提袋,带回家中,藏在梁上。武斗结束,钞票、粮票分毫不少送回门市部。这本来是一件“保护现金不受损失”的“功劳”,却因为武斗后“革命派”掌握了大权,居然把这件有功的事情说成是“违反现金管理制度”,愣是把她给下放了。
下放以后,她勇敢地到北京上访,睡火车站,闯国务院,居然让她拿到了巨大无比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信访办公室”的信封,装着“希当地政府慎重处理”的介绍信。她在当地的出名,主要是她的“勇敢”。但是浙南山村,天高皇帝远,当地政府并不因为有党中央、国务院的信而“慎重处理”,她的冤案,只是以回家以后大病一场而结束。
我遇见她的时候,她已经在食品站当临时工,还是当开票收款的营业员,月工资27元,比我这个“劳改犯”还少。
因为有这样的“共同遭遇”,所以我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颇谈得来。回到劳改农场以后,我们建立了通信关系。当时我正在偷偷儿地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括苍山恩仇记》,我把手稿寄给她看,她出于“爱才”,不顾我的劳改身份,不嫌我一个月只挣32元,愣是答应嫁给我。于是一年以后,1976年的12月, 我再次回到缙云县,和她举办了十分简陋的婚礼。1977年有了孩子,1978年她还抱着孩子到劳改农场来看望我。……
打倒四人帮之后,时来运转,1979年我先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工作;不久她也回到粮食部门。1984年,组织上照顾我们,把她调来北京,和我在一个单位工作。
二、心理的不平衡
但是我和她,却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我从小走南闯北,四海为家;她除了到过北京告过状,1984年以前的四十多年,主要在浙南山村度过。生活习惯和爱好完全不同。我是作家,以文学为事业;她只会打算盘,对文学一窍不通。她虽然“爱才”,但是她自己至少在文学领域是属于“无才”的人。
我们两地分居,倒是可以“各自为政”,互不干扰,一旦调到了一起,她的心理状态明显不平衡起来了。
在缙云当地,她是个“人才”。就凭她的铁算盘,许多单位都欢迎她去。北京调令来到,粮食部门的领导再三留她,只要她答应不去北京,一切困难都好解决。但是她为了照顾我,为了孩子有个北京户口,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优厚的条件,到北京来了。
我的单位,是个文学艺术部门。她虽然是出了名的“铁算盘”,但是没有会计证,无法上岗。再说,在北京当会计、出纳,根本就不用打算盘,都是用计算器。所以她来到北京,“人才”变成了“奴才”,只能让她打打杂,哪里临时要人去哪里“帮忙”。此外,她在粮食部门的“营业员”身份,到了北京,只能算是“工人”;而且她的每月53元工资,也是全单位中最低的。
这些遭遇,她心理上都不太平衡。但是从“一家团圆”着眼,这些问题,都可以容忍。特别是单位办起了内部食堂,让她当管理员,她倒是干得挺来劲儿。按说,管理员只管买菜卖饭票,但是她天天和炊事员一起做饭、炒菜,实打实地顶了一个“炊事员”的名份。因为她肯干,到了55岁退休,还在原单位拿“补差”,又干了好几年,一直到食堂散摊子,方才回到家里。
三、孤独:是她终身的遗憾
上班期间,哪怕心理有些不平衡,倒还不妨碍健康。她的得病,很可能是由于孤独而引起。尽管至今没有哪个医生说过孤独会引起癌症,但我总觉得生活的孤独对她有很大影响。
一般的离退休夫妇,大都是双双对对,一起逛逛公园,打打太极拳,聊聊家长里短。老伴儿老伴儿,主要是到了晚年,彼此有个伴儿。
我由于中年时代,劳改了23年,失去了最佳的写作时间,一心只想把失去了的光阴找回来。因此离休以后,离而不休,相反倒是进入了写作旺盛期:每天都在电脑前面敲打键盘,每天的工作时间,往往都在12个小时以上。特别是2008年,一口气写了十本书,总字数超过300万。这就把老伴儿冷落在一边儿了。以前,还每天早晨一起到公园去“遛早儿”;2008年以后,我只在家门口遛遛马路,最多半个小时就回家打电脑了。我一进入写作状态,就不再理她,她和我说话,我总是叫她不要打搅我。那一段时间,她天天吃过早饭就去菜市场,一逛逛到十点多才回家。买三个人的菜,当然用不了那么多时间,其实是她在家里呆着孤独,愿意到“人丛”中去走走。她曾经不止一次说:“当作家夫人真苦,还不如嫁农民。”虽然是气话,却反映了她的真实思想。
我这是用她的孤独,来换取我写作的“成功”。在这个问题上,我欠她的,实在太多,如今已经追悔莫及了。
四、病得奇怪,医得艰难,走得突然
她平时身体还算可以。由于挑食,比较瘦弱,还有贫血和低血压的毛病。2008年4月,体检查出盆腔骶骨有一个肿瘤,已经有11厘米大小。但检查报告说是良性,也不太着急。先到协和医院妇科住院,打算开刀。一切检查化验手续做完,第二天要上手术台了,忽然通知说“你的病不属于妇科,应该转到外科去”。但是他们不给转,只要求出院。我们通过关系进了肿瘤医院,经过检查,被告知:“你的肿瘤是从骶骨的骨头缝儿里长出来的,我们没有见过,不敢贸贸然开刀。建议转到积水潭骨科医院去。”到了积水潭医院,又被告知:“奥运会期间,要给运动员留床位。等有了床位再通知你。”在此期间,只能到国医堂吃中药。吃了半年穿山甲、鸡内金之类,病情不但不见好转,而且越来越严重了。医生不敢再开药方,要我们“另请高明”。我们再次到积水潭医院检查,肿瘤已经变为恶性,而且已经转移到肝、肾、肠,加上她严重贫血,既不能开刀,也不能化疗。最后给的一句话是:“不值得治疗了。”
这等于宣判她的死刑。但是总不能眼看着她在家里等死呀!通过朋友,找到了佑安医院的李院长。他是中国肝移植专家,佑安医院也不是治疗癌症的医院。但是他看在朋友相托的份儿上,答应“试试看”。他说:治疗癌症,有一种最新的“基因疗法”,也叫“介入疗法”。原理是:肿瘤与肿瘤之间,癌细胞是排斥的。如果把A肿瘤的癌细胞输送到B肿瘤中,两种病毒会互相残杀;再把向肿瘤输送营养的血管堵住,一方面让它们互相咬,一方面“饿”着它,肿瘤就有可能自己萎缩。
只要有医院肯收,我们绝不能放弃。于是在今年4月13日,住进了佑安医院。
第一次介入疗法是成功的。本应该半个月或一个月以后再进行第二次治疗。考虑到介入疗法的药物没到,医院建议我们回家疗养一段时间,吃点儿好的,养胖点儿,再回医院。
但是从6月30日出院到7月31日这一个月时间中,不知道什么原因,病人心情烦躁,拒绝进食。家里朋友送来的鸡蛋、牛奶、营养品堆成了小山,她就是不肯吃,吃什么都是一小口,第二口就不肯吃了。怎么劝,都没用。刚回家的头几天,还能自己走到厕所去,后来就要扶着走,再后来,自己站不起来了。6月31日,出现短暂休克,不久自己醒了过来。当夜就大小便失禁,语言不清。经与医院联系,8月1日叫120送回医院,进入“特护病房”,神志还很清楚,大喊大叫:“救救我呀!”8月2日去看她,已经进入弥留状态,眼睛虽然半张着,但是眼中无神,叫她也没反应,不认识人了。从此一直没有醒过来,直到8月4日早晨心脏停止了跳动。
在她住院期间,因为有女儿精心料理,我这个做丈夫的,依旧是“事业为重”,哪怕就是在病床旁边陪着她,也还是给朋友看清样,甚至把笔记本电脑搬进病房,帮朋友写序言,或者发博文。和她聊天的时间,还是很少。倒是她回家的这一个月,女儿值夜班,我值白班。她周身疼痛,我一连几个小时帮她按摩。特别是她大小便失禁以后,一晚上换几次尿不湿,都是我操作。结婚三十多年,夫妻一场,算是我“伺候”了她几天。
她对自己的恢复健康很有信心,我们也不便于问她有什么“后事”需要交代。所以一直到死,也没有留下一句话。我听到她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救救我呀”,但是已经无能为力了。
人总是要死的。新陈代谢,这是客观规律。但是摊上了癌症,就没有办法了。一个艾滋病、一个癌症,大概还是目前无法攻克的难关。如果癌症有药可治,估计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都不会死得那么早……
她,是个要强的人。如果她开公司、办企业,没准儿会成功。可惜她“爱才”,当了作家的夫人!
我,只能等我也到另一个世界去的时候,才能陪老伴儿散步、聊天了。
寄语老伴儿还没得病的离退休人员,趁着俩人还走得动,要多陪老伴儿走动走动,不然,可是要后悔一辈子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