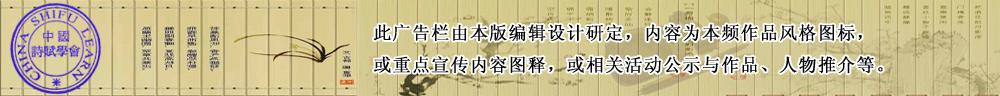
- 胜者为王【057】婶婶... [庄河教师]
- 【柳判传奇】̶... [羽砚]
- 美丽的逃亡(少年勿点)... [烽火]
- 17·天伦孽【草稿】... [羽砚]
- 我是你的稻草人... [皓月]
- 胜者为王【024】三个... [庄河教师]
- 31集电视和谐文学连续... [韦志远]
- 韦志远扶贫... [韦志远]
- 男奴(一)... [卡萨布兰]
- 恩施剿匪记 (二)解放... [云木欣欣]
|
1 田哥说没眼人也能辨清颜色,说罢便挺胸腆肚,举一双干瘪的眼窝洞察湛蓝的天空。我问他看见什么了。他说,医巫闾山,还有阳光。我又问阳光什么颜色的。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黑亮黑亮的呗!”表情神圣,不像玩笑。医巫闾山何年迁居天宇?阳光怎么会是黑亮黑亮的?我心中苦笑,田瞎子真是能扯! 2 然而,不久我竟相信,阳光确实有黑亮黑亮的那种。 田哥说他呱呱坠地时并非有别于任何男婴之处,也是起初哑谜,也是被产婆倒提两条细长的小腿,打了印有胎记的小屁股,才“哇”地唱出了人生的第一个音符,也是闭着眼高一声低一声地唱个没完。不同的是,唱着唱着,他那蚕豆粒般男子汉的圣物突然喷出一股热辣辣的液体,如丝似箭,直取产婆满是血污的“鹰爪”。瞬间,血污掺和尿液在气鼓鼓的小肚皮上画出了一幅玄妙的怪符。 产婆惊甚,接产三十年来,从未见过刚出母腹的男婴便能如此气壮山河地排尿。怔愣之余,霍地一道血光,那挣扎的小生命给掷到冰凉的土炕上。产婆被尿染得斑驳的“鹰爪”火燎般在腚后甩个没完。于是田哥便虫子一样在炕上蠕动,痛快地往身上印着美丽的炕席花。不知是出于何种心理,产婆总觉得被初生儿染尿非吉祥之兆。她不再瞥一眼这亲手接到世上的生灵,忿然离去。三天后,产婆死于非命。此时,田哥正翻着鸟蛋般浑然无光的双眼,给被烟火熏成枣红色的秝桔棚相面。人们就说这孩子有半仙之体。 田哥的口气显然是在告诉我他天生与众不同。然而我实在不记得曾褒奖过他有何才干。我觉得田哥的发达充其量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没有社会主义民政福利政策,没眼人当厂长不可思议。尽管是只有七名职工的蜡烛厂。 田哥递给我名片后,又准确无误地拽住了我的手,说:“要写就写我们整体,不要只突出我个人。我们厂七名职工,六个没眼人。我们自食其力,也给政府减轻些负担。我们生产蜡烛。我们心中渴望光明……”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嘴友好地冲着我的眼睛,好像我那里是麦克风。手又被他牢牢攥住,想躲也躲不开。于是我那可怜的眼睛被他嘴里喷出的大葱味虐待得饱尝辛酸。显然他是把我当成了新闻记者。采访这样的人一定会得心应手,只要你一点路子,他就会很聪明地按你所需要的线索滔滔地讲来,只要认真记录,稍加删改即可见报。可惜我不是记者。 当田哥知道我是税务所的人时,机械蠕动的嘴巴骤然拉了电闸,涩重的眼皮顽强地向上翻着。残疾人办企业是免税的,但他心中有“病”,我的光临不受欢迎已在意料之中。 “二菠菜,二菠菜?”田哥突然举着嘴冲天棚喊。仿佛那里藏着什么二菠菜,却仍不松开我的手,好像我是被他好不容易才抓住的小偷,生怕跑掉。 应声而入的是个鲜鲜亮亮的女孩,二十来岁。果然是棵水灵灵的菠菜,翠嫩欲滴。 “二菠菜,这个税官兄弟哥咋不认识?谁家的?”田哥把嘴冲二菠菜伸了伸,同时晃晃我的手。 二菠菜那菠菜根一样粉嘟嘟的脸转向我,明澈的双眸盯盯地看着我。残疾人工厂里竟有如此鲜艳夺目的女孩?! “厂长,我也不认识,好像不是老户。”二菠菜甜甜地对田哥说,一双秀眼却始终在我身上滚。 难怪田哥这么问,在这不足万人的小镇上,人们相互了解的程度不亚于熟悉自己的手纹,更何况那屈指可数的几个政府官员啦!我告诉田哥,我是前两天刚从县局调来的。田哥恍然大悟似地松开我的手,连声道:“新来的税官?失敬!”接着他说:“这位税官兄弟,你不是省里派来调查啥事的吧?!” 我说:“我说过了,我是县税务局刚调来镇所的。不是来调查啥事,是常驻。” 我的回答似乎令田哥很扫兴。片刻,他又高兴道:“常驻好!常驻好!咱们镇所也真应该加强力量啦。税官兄弟,今天光临我的小厂是想帮朋友批发点蜡烛吧?这货眼下出手快,城里更快。三天两头停电。就等一拉闸,你就走街串巷地卖,一会就弄个十块八块的,不知咋整的,物价像小孩鸡鸡似的年年见涨,靠那点工资不是扯嘛!税官兄弟,你来买没得说,出厂价再优惠你两折。二菠菜,给税官兄弟开票。你姓啥来着?提货捡好得拿。” “不,田厂长……”我打断他的话,并告诉他我姓伍。 “哎!什么厂长,屁大个厂!伍税官,你就叫我田哥吧,镇上的人都这么叫。” 田哥就田哥,于是我就叫他田哥。我稳定了一下情绪,告诉田哥,我是接到了举报信才来找他的,想核实一下。 没等我说完,田哥竟然炸了,那双干瘪的眼皮像滚水烫开的牡蛎,两只鸟蛋样的眼球茫然而混沌。他恶声道:“揭发我?跟没眼人做对算个鸟能耐!有种冲腐败去,谁干这事让他下辈子托生瞎子……”田哥拂袖而去,在办公室门外又停了下来,头也不回地喊道:“二菠菜,还不干活去,傻愣着什么!” 二菠菜踌躇片刻,还是去了。临出屋,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冲我抛出了一串暗示。可我什么也没读懂。 3 我有一位表哥在田哥的厂里当顾问,关系不疏也不密,他一直反对我插手蜡烛厂的事,这天,他友好地挖苦我一顿:“小伍子,这头把火烧得不错吧?田哥是什么人,你敢去惹乎他?你知道他手里有几张牌?” “管他有几张牌!政府照顾残疾人,不纳税就够意思了,你们还钻国家空子。举报人也不光冲田哥,主要是张子立。”我说。 “这个张子立就好惹吗?”表哥款款地吐着烟圈,款款地卖关子,许久,一个圈一个字的往外挤,“那是县太爷的三公子!” 我虽刚出校门不久,可世事艰难也略懂一些,我索性不与他理论,换了个话题:“那个二菠菜……” “喔,她是西街吴大鞭杆子的二姑娘。吴大鞭杆子够废物的,一辈子没造出个儿子。不过四个姑娘都挺水灵,数老二最绝。那四个丫头的名绝了:大红枣、二菠菜、三青杏、四白梨。吴大鞭杆的女人怀孕时,害口想吃啥就给孩子起啥名。你不是看上二菠菜了吧?我告诉你,那可不行。不是表哥干涉你的私生活,那女人太骚性,太骚性,不配你这个研究生。千万莫去惹乎她,当心倒霉。” 4 据匿名举报信上介绍,张子立在外地办了个地下黑工厂,也生产蜡烛,然后以田哥厂的名义批发,偷漏税款。案情就这么简单,又十分复杂。复杂的是田哥对此矢口否认。尽管我已初步查出了他们六位盲人的生产能力远远达不到账上的数目。张子立黑工厂生产的蜡烛显然是抢了田哥的一部分生意,可田哥竟甘心为他效力。是田哥也从中渔利,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这正是我下一步认真核实的事。我要求全面查一下二菠菜的账目。田哥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任我去折腾。田哥眼皮一翻道:“二菠菜会记什么鸟账!盲人工厂账也是瞎的,全凭良心办事。都在我脑子里,你钻进去查吧!” 这显然是依残耍蛮。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吼了起来:“良心?你有良心就不该这种态度!没有社会主义民政福利政策,你这瞎……”我突然感到自己不该这样失态,收住话茬,“对不起,我太激动了。” 田哥似乎没因我的言语不恭而恼怒,反之倒沉默下来,沉默得连眼皮都不翻,低头听我一人讲。 说实话,我没半点整治田哥的意思。我在心里都想过,如果真查出是张子立与田哥合谋偷税,我也会不同程度地袒护田哥。这可能是中国人助弱除霸心理的反映。我耐下心来规劝田哥。暗示他只要说出张子立的名字,绝不再为难他。想不到田哥这一沉默就是两个多小时。这办法来得更是厉害,令我哭笑不得。面对这十几万的偷税案,我深感势单力薄。 领导派给我的伙计因母亲丧事走了,再无新人可派。无路可逃,只能干下去。 我的行动在镇里引起了一场风波,别有用心的人趁机四处造谣,说我的举动无非是想搞名堂,想当所长。上面把我安排来就是有目的的等等。我实在难以享受那些人对我的恭维。我暗暗下决心,这个案子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于是我把搞清田哥税案当成在小镇立住脚的关键所在。我到处找人调查、取证,以图获得更多的一手资料。 该取的旁证取得差不多了,却无法深入。我只好向所长汇报。 所长看了材料后似乎也很难。他说证据不足,无法立案。还说等我那位伙计回来再说,暂时不可擅自行事,不满之意溢于言表。 我第一次感到小说里的英雄壮举都是他妈胡说八道,在生活中根本行不通。我悔不该自恃聪明,有魄力,把生活看得那样美好,梦想到基层轰轰烈烈干一番,到头来弄个画虎不成反类犬。凭我的学业,我的能力留在县局机关当个好科员绰绰有余,熬个三年五载弄个科座当当也大有可能。可这一切都晚了。我不知道这伟大的失误该归功于谁。归功于我的利令智昏自我感觉良好,还是压根儿选错了行当? 5 半瓶吉林原浆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瓶中水位在不断下降。花生壳鸡骨在桌上无声地肉搏,惹来几只不甘寂寞的苍蝇嗡嗡助战。 从来小镇那天起,我就起誓滴酒不沾。这不只是因为我酒后失常,更怕吃人嘴短。可如今到了这个份上,除了与杜康把盏长谈还能怎样? 此时张子立他们可能早已酒足饭饱,或剔着牙搓麻将,或搂着不是媳妇的女人。可我呢?办公室又是家又是宿舍。一张折叠床折了支支了折。 天是在瞬间黑下来的,像中了什么魔法。山村小镇就是这样,太阳在西山梁上趴着,像一只没煮太熟的蛋黄,捎一震动就滑了下去。小镇没有黄昏。于是街灯按时顶班。于是该响得响该亮得亮。于是街心那代表现代气息的舞厅就嘭嚓嘭嚓。 亮灯到停电不过一袋烟的工夫,小镇又黑下来,好像比亮灯前黑了许多。街上的人们就骂,舞厅里的人骂得更甚。他们骂电业局停电不通知,又骂舞厅老板明知停电还卖票又不给退。人们就这样骂着骂着散去了。当然,明天他们还要到舞厅来,尽管不知道是不是还停电。 小镇出现了一天内少有的平静。可瞬间又传来了另一种声音,是卖蜡烛人的吆喝声。吆喝声几乎同时从镇街东南西北传来,又彼此呼应,像是一个人在山谷里的回声。这些卖蜡烛的都是田哥厂里的盲工人。每星期都要有这么几回,赚的利钱全归卖主。于是这些盲人便漫天要价。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人买,除夕夜送酒壶,正等着呢。再说,没眼人给有眼人送来光明,在感情上总觉得过不去,哪还好意思讨价还价。最不济说家里有蜡烛,刚买了几天。卖主就会劝你买下再买些又何妨,日后停电就像眨眼一样频,蜡烛放在家里不吃草不吃料,也不腐烂,当心涨价哩!盲人嘴都会说,说了就把成包的蜡往你手里塞。于是买主就得悻悻地掏钱,还得说一两句迎合着的话。小镇上的人没人愿意得罪这些盲人。田哥蜡厂成立前,这些盲人大多是算命先生,有半仙之体哩! 盲人拿了钱,边用手摸索着数。边噌噌地在黑暗中行走,继续吆喝,比有眼人走得快。盲人的世界没有黑暗。 我不知道怎么就趴在桌上睡着了。朦朦胧胧觉得屋里有烛光。细听来,街上盲人卖蜡烛的吆喝声已消失,我不记得什么时候买了蜡烛,怎么又点着了。我前面的桌面已收拾得很干净,那四分之一瓶的吉林原浆正立在上面默默地注视我。折叠床也铺好了平平整整的。我不敢肯定这些是不是自己干的。我一喝多酒就出现幻觉,以前也有过这事。 我趔趔趄趄爬上床。不知是弹簧床太软还是喝得太多,我就像跌进一条小船,不停地摇来荡去。烛光也跟着我摇,淌得满屋子都是。荡来荡去门就给烛光撞开了。一个女人借这工夫飘了进来。以前在酒后幻觉中也出现过女人,这回又出现了。幻觉中出现女人总比出现魔鬼好。我很平静。 女人的影子被烛光夸大地甩下半面墙。她穿了件很宽松的白色或藕荷色的衣服。烛光里辨不清颜色。她下身好像只穿着自己的影子,黑裸裸的胯、臀、腿。她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很惊诧,不光是因为她美,还觉得她面熟,在哪里见过,好像是梦里,女人有些怕羞的样子,可还是主动跟我说话。说得什么我没听清。然后我就平静地看她为我宽衣,又看她自己脱,看她娇羞地把灯吹灭了。 接下去我们好像干了男女间那事。那事以前在幻觉中也干过。 6 好像是一把大钳子似的东西钳着我的两只太阳穴,痛得我两眼冒金星。艰难地睁眼一看,却是一束从窗角斜刺进来的晨光,棒子一样抵着我的脸。我竭力推了两下那光柱,推不走,索性坐起身用力揉着太阳穴。沾酒必大醉,大醉必出幻觉,醒后必头疼,这是我的醉梦三部曲。 我竭力回忆夜里的幻觉,却只能断断续续地寻回些零星碎片。如同被蹩脚的摄影师胡乱剪辑的一部纪录片。那曾统治我的幻觉已全部消失,唯有半截蜡烛仍立在我的眼前,不再流淌的泪成了凝固的记忆。 表哥来找我了,他神神叨叨的问我:“田哥叫你啥事?” “我怎么知道?”我说:“他什么时候叫我啦?” “啊,我刚在街上碰到他的,带信让你去一趟。”说罢,他拍打着身上的尘土往外走,走到门口又站住了,回头对我说:“你千万别去沾二菠菜,小心倒霉。” 田哥准是对张子立的偷税案有了认识,急着找我去谈些什么。我饭也没吃就去找他,不然酒后也没胃口。 田哥的耳朵灵敏得令人震惊,我刚进院门,他就在屋里冲我喊:“来了,伍兄弟?快屋里来!屋里来!”我踏进门槛的一瞬间,手已被他牢牢捉住,他三扯两扯就准确无误地将我塞进沙发里。田哥松开我,用袖头飞快抹了抹茶几面,翻着眼冲门外喊:“二菠菜,二菠菜?” 二菠菜应声而入。她扎着白花蓝地的小围裙,忙着往屋里端着饭菜。她脸红红的,一直羞涩地避开我的目光。端完饭菜她再也没有出现。 茶几上的饭菜令我胃口大开:大米绿豆粥、五香花卷、四碟精致的小咸菜。这鬼精灵的田哥好像知道我昨晚喝多了酒,他翻着白眼珠子冲我得意地笑。“绿豆粥解酒,小咸菜爽口,得意吃管够,全是二菠菜的巧手。”田哥像在说数来宝,小字眼咬得合辙押韵。说罢便吸烟,侧着耳朵听我吃。 显然他已知道我昨晚喝醉了酒。小镇上的人们都说,没有能瞒住田哥的事。田哥有半仙之体,能掐会算。他曾是这一带算命瞎子的头,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邻里纠纷,红白喜事总少不了求他去出谋划策。也是怪,人们大多都信他的,他的裁决具有权威性。听说“史无前例”那年,有个造反派头子不信那套,对田瞎子说,你给我算一卦,算准了往后我不管你,算不准就砸了你的算命摊。 田哥想了想对他说:“闭门躲三日,出户有灾星。” 那造反派不信,偏偏到大街上去逛,结果第二天就被武斗飞来的流弹打死了。从此小镇上的人们更把田哥视若神明。 有关田哥这方面的故事我听了不少,心里也猜疑,可此时却有几分相信了。他的神态和口气不容我假斯文地推说不想吃或已吃过了等等的谎话。更何况我的喉咙里就差没生出一双小手。于是我便喝粥,便吃咸菜,便咬花卷。粥喝得吱吱响,咸菜咬得咔咔脆,花卷在我嘴里呜噜呜噜叫。田哥听着煞是惬意,像在听一首美妙的乐曲,习惯向上举着嘴巴,孩童一样兴奋地闪着光。 吃完了,田哥没有吆喝二菠菜拣碗,而是把我扯过来,一并坐到炕沿上。我知道我的眼睛立即又要遭他嘴的虐待了。知道也得挺着,这就叫吃人嘴短。于是他嘴就对着我的眼睛说:“这事都是哥的主意,要怨就怨哥。二菠菜是个好姑娘,你千万别以为她这是轻浮,这绝对是第一次,你应该知道,哥也是无奈才出此下策……” 我不知道田哥在说些什么,更不知他出了什么主意。我显得懵懵懂懂的。田哥就火了:“伍兄弟,你挺聪明个小子,装傻也不分个对象。阴天下雨不知道,自己干啥事还不知道?”说罢就扯着嗓子喊二菠菜。 二菠菜进来了,忸怩地立在门口,脸羞红,葱白似的手指在小腹前纠缠,眼里先是汪着两股泉,我的目光一触动,那泉溪冲开了我记忆的闸门,梦幻中零星的碎片重新拼凑、组合,凝固的烛泪开始稀释…… 那该死的夜晚! 那该死的不是梦幻的梦幻! 那该死的吉林原浆! 7 吴大鞭杆的四个姑娘三个待嫁在家,老婆是个有二十多年哮喘史的病篓子,全部生计都维系在吴大鞭杆手中的鞭子上。 这些年国家政策好,人们的生路就宽了许多。从毛驴车、单骡车到三套马车,这里记录着吴大鞭杆的兴家史。吴大鞭杆子赶了一辈子马车,终于有了自己的牲口。虽然到他现在还欠着信用社几千元贷款,可有了家业兴旺的兆头,就不愁还债。晚年的好生活抵销了他终生无子的遗憾。从镇里到县里,从县到省城,吴大鞭杆的鞭子好不威风,马铃声好不响脆。虽说眼下已进入了拖拉机和汽车的时代,吴大鞭杆却更喜欢大车。铁牲口咋也不抵肉牲口通人气。汽车拖拉机能拉的货他能拉,汽车拖拉机不能拉的货他也能拉。吴大鞭杆拉脚又快又稳,从未出过半点差错。县里镇里大工厂小企业,都爱雇他的车。 于是吴大鞭杆的车赶得欢,票子进得多。他给老伴买最好的哮喘药。他把闺阁待嫁的三个姑娘养得小葱似的,令镇上的男人们垂涎欲滴。 可忽然有一日,吴大鞭杆的大车竟然再无货可拉,三匹膘肥大马闲得在院里趵蹄。红缨鞭成天吻着山墙,吴大鞭杆急白了头发又急白了眉。他百思不得其解,只得闷在家里喝烧酒。他哀声叹气地喝得欢,老伴弓着腰在炕头便喘得急。喝着喘着我表哥就来了。 他说他听说吴大鞭杆没了生意,过来看看,他还说他有个朋友在县里,挺有权势,兴许能帮着找点活。 吴大鞭杆急着问这人是谁,表哥就说出了张子立。说张子立是县太爷的三公子,哪个工厂企业不给点面子,一句话就有吴大鞭杆干不完的活。 吴大鞭杆听了就兴奋得像个老顽童,跳过来求表哥帮着说话。说事成之后一定重谢。 表哥问怎么谢,说人家张子立不缺钱花。 吴大鞭杆急着问,那怎么办。 表哥就用眼睛往屋里瞟。那里二菠菜正对着镜子梳妆打扮。吴大鞭杆就明白了一切,酒盅越发举得频,炕头的老伴越发喘得欢。 吴大鞭杆说门第悬殊,不敢高攀。表哥说倒谈不上高攀不高攀,人家张子立早有妻室,孩都三岁了,泰山大人是省城里的官,他是看上了二菠菜的小模样,想做个相好,眼下叫情人,正时兴这个。 于是吴大鞭杆的酒瓶子就粉碎了,酒气缠着怒气在屋里撞。“我姑娘不给别人当小老婆,要找情人上窑子。” 表哥被呛得直卡巴眼,讪讪道:“又没人逼你,干啥这大火气?好多人想攀,人家张子立还看不上呢,好心当成驴肝肺!……” 表哥走了。吴大鞭杆像头暴怒的狮子在笼中冲撞。老伴便像条出水的鱼,张着大嘴出气多进气少,一双眼憋得幽亮,满是焦急和绝望。 吴大鞭杆子大字不识两口袋,却能读懂妻子的眼神:全家五口人等着吃饭,信用社还有几千元贷款,我这该死的病篓子死又死不了…… 吴大鞭杆最见不得老伴的绝望。老伴是为他拼命生儿子才落下的哮喘病。尽管儿子终于没生出来,可她没有功劳还有苦劳。他是老伴的全部希望,老伴也是他的生活寄托。用不了几年,三个丫头都得他妈燕似的嫁人飞走,到时还不是俩老家伙熬灯为伴?想到这吴大鞭杆就把酒盅捏个粉碎,就不是动静的喊二菠菜出来。 二菠菜在里屋听得真切,泪泡着眼,泉涌过腮,梨花带露,怨怨艾艾。酒盅在地上被摔得粉碎,爹手上的黑血滴落着。一个暴怒的声音狂叫着:“没事到街上招风,这回惹下祸了。自己梦自己圆,自栽的苦果自家吃。反正好端端的家不能毁在你的手里……” 二菠菜的心颤抖了,生活为什么逼她付出无谓的代价?!她疯也似的跑出屋去。 她能跑到哪里去?她能逃出生活的魔圈?她还有最后一线希望?那就是去找田哥。镇上谁家有事都找田哥。找田哥的事不好办也好办;不找田哥的事不麻烦也麻烦。人们都迷信田哥。田哥也认真地管,无论有没有交情,只要求到门下。 二菠菜呜呜地哭述。田哥皱着眉翻白眼。显然这是件棘手的事。二菠菜第一次看见田哥这般为难,心就像出炉的铁,一会比一会凉,可还抱有一线希望——天下没有难倒田哥的事。 田哥果然不负所望,他问二菠菜有没有心上人,他可以立即组织他们完婚。二菠菜出身卑微却心比天高,她一心想寻个有理想,有知识,又没有铜臭味的后生为夫。退一步说,就算在小镇找个男人草草嫁了,张子立岂能罢休?还不是成全不了爹的生意? 事情果然太棘手。一头是县太爷的三公子,一头是心地纯真的姑娘。可怜田哥一双瞎眼忙上忙下地眨,终于眨出一条高道道。 张子立被请来了。 表哥也被请来了。 二菠菜忙前忙后弄了一桌子酒菜。 田哥把酒杯举过头顶:“二位兄弟先听我说两句。哥今年四十大几了,虽说眼瞎,却也是男人身子,又至今未娶,田哥相中了二菠菜,没想到跟子立兄弟抢了一个槽子。今儿个请二位来,就是想商议一下,能否把二菠菜让给哥哥。哥哥是没眼人,娶媳妇不易。子立兄弟一表人才,再加上令尊的权势,还怕相好的不往你被窝里钻?” 一席话弄得表哥和张子立面面相觑。方圆几十里,田哥仗义出名,谁不敬他三分?张子立也是地面上的人,只得苦笑相让。 田哥敬酒三杯,以谢相让之情。干罢,袖头抹嘴,田哥又求一事,“吴大鞭杆的生意日后还全凭子立兄弟打点。” “这……那是,那是。不过……”张子立欲言又止。 “有啥难事尽管和田哥说,只要能办。”田哥把胸脯拍得哐哐响。 “这事你办起来易如反掌,早就有意相求。”张子立饮下一杯,“不瞒田哥,老弟也开了家蜡烛厂,这货想打着你们厂的旗号往外发。说明了就是为了少交几个税钱。当然也少不了你老兄的好处费。”张子立说得煞是轻松,仿佛就是仨瓜俩枣的事。 田哥却肃穆起来,眼不再翻,嘴不再举,俨然一座蜡雕像。 “田哥放心,绝无半点风险,只要我老爹在位。”张子立说。 “就算万一出事,有我兜着呢,能把你个残疾人咋样?”张子立接着说。 “这点事田哥连面子都不给,就休怪兄弟无情,吴大鞭杆的生意……”张子立又说。 于是蜡像般的田哥就啪地一掌拍在桌上。 于是张子立的蜡烛就打着田哥蜡烛厂的旗号塞进市场。 于是二菠菜就在田哥蜡厂当了会计。 于是表哥就到田哥蜡厂做了顾问。 于是吴大鞭杆的马车就有货可拉。 8 这一切都是二菠菜向我哭述的。她说田哥当着别人的面说跟她好,其实从未碰过她一指头。她说田哥总问她找没找到意中人,找到了就为他们主婚。她还说,若不是我的出现,她可能下决心真的嫁给田哥啦。二菠菜说她喜欢我,看第一眼时就喜欢上了。说我就是她梦想的人。二菠菜把自己的爱慕之情全告诉了田哥,还说担心我表哥从中作梗。于是田哥就为我精心地设计了那场梦幻,二菠菜说她知道这么做不光彩。可为了所爱的人值得。她说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若不是既成事实,我绝难挣脱你表哥的干扰,因为你表哥不单是个势利小人。 然后二菠菜问我喜不喜欢她,愿不愿意娶她。我觉得她这话问得太晚,事情却做得太早。那场梦幻设计得再精彩,再令我回味也是对我人格的亵渎。爱是彼此心灵的呼应,绝不是一厢情愿。尽管她长得很美,我也喜欢看她。但我这人天生就讨厌被别人指使、强迫着去做什么,就连我心中也曾想做的事也不例外。 我无法回答二菠菜的急迫目光。我要让她知道我毫不顾忌梦幻中的既成事实,至少应该先打消一下她那居高临下的情绪。于是我不知怎么就挤出了一句话:“自作多情!”我为我说出的话感到吃惊。既已说出了也不好收回。想收回也不能是现在。我转身离去。我听到身后二菠菜呜呜地哭,好不伤心凄惨,仿佛到了世界末日。 可我终于没有回去劝她。 9 还是黑得夜。停电。小镇上听不见卖蜡烛盲人的吆喝声。替而代之的是一伙伙举着火把的人群。说二菠菜不见了,天一黑就不见了,怕是寻了短见。是田哥召集人在寻。 我的心不由忽悠起来。二菠菜寻短见的原因怕数我最明白。我真恨那句溜出嘴的“自作多情”。一瞬间我成了罪人。 我急忙加入了寻找二菠菜的人流。岗上,坡里,沟下无一处不寻遍,连没膝深的小河都躺了无数个来回。一寸寸地摸,一寸寸地看,哪里也不见二菠菜的影子。 直到天不再那样黑,火把不再那样亮,人们才在镇西菜地一眼多年不用的老井里找到了二菠菜。二菠菜半浸半浮地仰在水面,一息尚存。人们呼天抢地地将她捞上来,立即送往县医院。是我害了二菠菜,负罪的内疚感像针芒刺痛在心。望着拉走二菠菜的拖拉机,我突生个念头:如果二菠菜能生还,我定要娶她为妻,并请田哥证婚。 想到田哥,便听见有人惊呼井里还有双手。于是五六支手电就同时把灰洞洞的井口照得雪亮。果然井水里若隐若现地有双手在晃动。忙着又是一阵打捞。人们惊呆了,想不到打捞上来的竟是田哥,更想不到死去多时的田哥仍木桩般立于水中,双手直愣愣地举过头顶。此时人们才清醒,是田哥在下面举着二菠菜,否则落水不久的二菠菜没有理由浮在水面。 田哥的尸体躺在井口旁,双手直直地举着,五指叉开,眼睛向上翻,像在够着什么永远够不着的东西。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将他的双臂搬回原位,可一松手,那双臂又弓一样弹了回去。直到入殓时田哥都是举着手去的。 10 田哥死后约两星期。一辆黑色奥迪轿车开进了小镇。不久小镇就传出了一件令人震惊的消息:省城纪检部门来人了,来查张子立和表哥的事,是田哥生前写的举报信。原来表哥与张子立是一伙的。 作为税务人员,我有幸参与了侦破张子立的税案。一同工作的纪检干部对我说:“这封信一年前就收到了。因为是用盲文写的,信访的同志不认识,就给压下了,直到前不久进行工作大检查时才重视起来,请盲人教师翻译过来。这事我们有责任……” 于是我就读了田哥那封举报信的译本: ……这封信本该寄给镇纪检委或县纪检委,可在县里这块地盘上到处是张家的耳目,弄不好告状不成反遭蛇咬。为此我才把信寄到省城,而且用了盲文(怕求人代写走漏了风声)。这封信也可能石沉大海。但我坚信,只要是共产党的天下,总能找到阳光,黑亮黑亮的阳光。张子立给我的好处费都存在我的账上,一分没动。我眼瞎心不瞎…… 11 我和二菠菜结婚了。可惜证婚人不是田哥。 |

诗赋绽芳蕊 今来觅知音
版权所有:诗赋网 Copyright 2008-2016 zgshifu.com All Rights Reserved 辽ICP备18006388号
诗赋杂志投稿邮箱:sunwulang@163.com
联系人:轻盈 QQ:418193847、1969288009、466968777 QQ群号(点击链接) 电话:15609834167 E-mail:sttsty@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