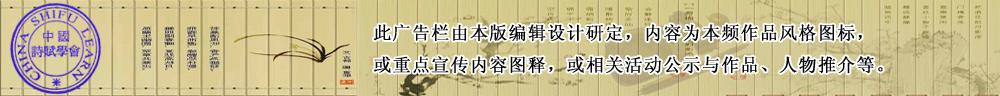
- 胜者为王【057】婶婶... [庄河教师]
- 【柳判传奇】̶... [羽砚]
- 美丽的逃亡(少年勿点)... [烽火]
- 17·天伦孽【草稿】... [羽砚]
- 我是你的稻草人... [皓月]
- 胜者为王【024】三个... [庄河教师]
- 31集电视和谐文学连续... [韦志远]
- 韦志远扶贫... [韦志远]
- 男奴(一)... [卡萨布兰]
- 恩施剿匪记 (二)解放... [云木欣欣]
人们大多数是用眼睛看别人,如果用心去看,那么,映入你人生底片上的显影和瞳孔中的折射是不完全一样的。
——题 记
1
去年夏天的地球,像烧烤摊上的鸡架,在烤炉上无休止地翻弄熏烤,于是乎,满世界的人都成了离开南极的企鹅,扎煞两只小膀盼望凉爽。二两散白干,一缸酽茶,成了我入夏以来的晚餐保留节目,谁不知道冰镇啤酒更美,可是喝得起吗?金融危机,物价飞涨,工厂大多处于半停产状态,在家稳坐,能喝上散白还多亏老婆在“外资”企业当工人。老婆一天累得够呛,难免有意无意地半开玩笑半发牢骚地说:“看人家老爷们都干点啥,哪有你这么泡在酱缸里当‘咸’人的?”其实我也想铺个摊,混个毛八七的,但底气不足,只好望“海”兴叹。
巴黑子突然来访,着实令我惊诧。等他说明来意后,我简直就不认识他了。
巴黑子是我小学同学,一晃也有20来年没见面了。在校时我是一碟小菜,他还不如半块青方,只有他那杰出的大下巴和比泰森还白点的皮肤给我印象最深。他一向寡言少语,从没听说他说过一句完整的话。这回也是一样,啪,一沓钱甩给我:“做买卖。伙!”
再笨的人有时候也露出点聪明,关键在于对比。在巴黑面前我觉得比他灵气多了,和他做买卖岂不降档次。偏偏老婆看中了巴黑子,说他诚实,合伙干放心,况且还有那三千元底钱(过后我想,说不定巴黑子就是老婆找来的)。
“那就干呗,干啥买卖?”“西瓜!”巴黑子用手做了个砍瓜姿势,“挣了对半分,赔了算我的。”这条件,使我无法拒绝。真别说,这小子还有点脑子,今年夏天火炉子一样热,卖西瓜还算对路。
在小市场上租了一间没有四壁的铁棚子。一大车西瓜卸进棚子,我们的买卖就开张了。干过三五天,算完帐,真的赚点钱,告诉他,他只是“呵!呵……”不往心里去。简直一切都是我说了算。每到晚上西瓜卖得最快的时候,我一手大蒲扇,一手宰瓜刀,真好像快活林的当家的,我很得意,觉得自己原本也是个很不错的生意人。蚊虫扑向瓜棚的200度大灯泡,也昏头昏脑地往我脸上扑,越是忙不开,巴黑子却不露面,我下定决心,等收摊后,他回来我非得大骂他一顿不可。
巴黑子回来的时候,正是我数钱的当口,骂人的腔调自然显不出火气,巴黑子不理会我在骂,钻进蚊帐打起鼾声。虽说晚了,睡前我还是喝一遍酒。从对面熟食店里买几两猪耳朵和油炸蚕豆,关了灯,慢慢品嚼。坐在黑暗里望着灯光闪烁的市场,觉得棚子外的世界的小店铺把自己的故事神秘而逼真地装进灯光里,供我从头阅读。
熟食店的隔壁是修锁配钥匙的;他的隔壁是家洗涤店,紧挨着一家小饭店;我们瓜棚的一边是一家寿衣庄,另一边是一家成衣铺。寿衣庄的老板年近七十,老头子脸像注了水的白条鸡,大白眼像死羊一样朝上翻。“寿衣”不像“熟食”和“钥匙”那样平易近人,总是死羊眼向上不理人。半个月来,我发现他唯一去的地方是我们瓜棚对面的小饭馆。这小饭馆的老板娘三十多岁,颇有几分姿色,但见她出出进进忙活,从不光顾我们的瓜棚。二两酒进肚,我想睡觉,一脚踢醒巴黑子:“有偷瓜的了!”他爬起来去撒尿,我乘机钻进蚊帐。
睡到半夜下起了大雨,铁棚子漏了,我跳起来喊巴黑子,巴黑子却像黑猩猩一样蹲在对面小饭店的屋顶向我招手。
2
那一刻我简直气炸了。几百斤西瓜在洗澡他竟不顾,跑到小饭店房顶上学雷锋。大雨瓢泼似的,喊他也听不见。一道闪电划过,我才发现他身子压在一块塑料布上,手向我比划。我猜想是向我要砖头。给他扔几块砖头吧,否则看架势雨不停他不会下来的。砖头砸在房上,惊动了小饭店的老板娘,灯亮了,从窗户探出头来:“谁呀?上房折腾什么!”那口气满酸满横。我见她那口气就不自在,顺口扔出两句:“干什么!你房漏了,帮给苫塑料布哪!”
这会儿巴黑子猴子似的从房上跳下来,浇得像落汤鸡,比哭还难看地冲着老板娘龇着牙赔笑说了一句含糊不清的话:“不漏,不漏!”老板娘骂一句“精神病!”啪地把窗户关上,熄了灭。我气得照着巴黑子那油桶似的肚子给了一拳:“你他妈的发贱呀!”没曾想正打在巴黑子的痒处,他竟跺着脚在雨中狂笑:“哈……哈……跟我说话啦!”巴黑子的笑声使我发毛,我也听不明白他话的意思,直觉得他真有“精神病”似的。
大雨过后,水浇的西瓜放不住,一算计损失了二百来元。巴黑子根本不往心里去,又进了一车西瓜。
从此以后我觉得巴黑子不是一根木头,显然是爱上小饭店的老板娘了。这一发现使我震惊了,因为那老板娘端庄秀气,可不一般,巴黑子岂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后来我发现,每天晚上那段卖瓜的黄金时间,巴黑子却钻进小饭店里,一碟菜、一壶酒地坐到闭店。
一天,我老婆吃过晚饭来看我,我让他替我看着瓜摊,径自走进小饭店。我第一次来这里,觉得这小店虽不豪华却很雅致,像老板娘那容貌一样,秀美可人。
见到我进来,坐在墙角的巴黑子霍地站起来,想溜。我大吼一声:“巴黑子!”
巴黑子被我喊声钉住,原地未动。我走过去坐下,点了几个菜,要几瓶冰镇啤酒。巴黑子憨头憨脑地随着我的手势又坐了下来。
老板娘和那个服务小姐风摆柳似的来上酒上菜。这回离近了我仔细端详一下老板娘,那白嫩的皮肤像十八九岁的姑娘,她一转身从我身边走过还带一股香气。巴黑子呀、巴黑子,这漂亮的娘们能看上你吗?你犯单相思呀!
巴黑子是我小学同学,人太老实,我要帮他,让他从美梦中醒来。于是我主动与老板娘搭话:“老板娘,怎么不见老板呐?”老板娘脸一红,服务小姐把话接过去。“人家是大学问的人,哪能到这来。在家写书哪!”
我把目光瞥向巴黑子示意他:“人家是有夫之妇了。”可恨巴黑子根本不懂我的目光,只是傻笑。我忽然发现寿衣庄的“死羊眼”坐在另一个墙角不怀好意地用眼睛翻我们。其实这两天附近的几家都看出巴黑子对老板娘的用心,“钥匙”和“熟食”也不时来逗巴黑子,人家总不吱声,从不来瓜摊,和我们碰面时也一闪而过,好像不认识似的。
世上的事有时也很有意思,有的人以得到为满足,而有的人则以看到为满足。巴黑子就是后者,只要坐在小饭店里看着老板娘出出进进忙活,他就满足了,和老板娘从没说上一句完整的话。就是遇上重活,比如搬啤酒箱子,他就不声不响干,然后不声不响地离开。
一天夜里,我起夜,突然发现寿衣庄的“死羊眼”钻进了老板娘的小饭店。我一急,赶快把巴黑子喊醒。
3
我不知那一刻为什么要喊巴黑子。可能这就是真作假时假亦真,我觉得巴黑子理所当然要对老板娘负什么责任。
巴黑子果然心中揣着神圣的责任感,听到我的叫声,他轱辘爬起来,狼一样扑向小饭店的门,抡起拳头一阵砸门。门开了,灯亮了。巴黑子拖着大下巴,霜打着脸,不顾一切地冲进屋去,狗一样连窥带嗅,死羊眼终于让他在门后给揪出来了。巴黑子两眼怒火,揪住“寿衣”冲老板娘啊啊地叫。老板娘吓得脸色死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巴黑子爱得太痴了,从没见他如此动过气。
我拽开巴黑子的手:“你是老板娘什么人呐?管这干什么?”
一时间我也糊涂了,既然不愿让他管,干嘛还要叫醒他?
巴黑子没有因为我的话而消气。他一把将“死羊眼”搡倒在地上,又指着老板娘的鼻子呜噜了好一阵,甩身而去。一连五天巴黑子没回瓜摊来。我想他是不愿再见到老板娘。是呀。看着自己痴爱的人和别人染指,是男人受不了的。
出那事的第二天,老板娘也不见了。小饭店只有服务小姐和厨师支撑着。第五天晚上,也就是巴黑子突然回来的那天半夜,小饭店的服务小姐冲出店门疯喊:“不好啦!老板娘自杀了!救人呐!”
首先惊醒的是我和巴黑子。巴黑子第一个冲进小饭店。老板娘横躺在餐桌下,桌面上放着四支空着的敌敌畏瓶子。
那一刻巴黑子惊傻了,他呆愣愣地望着面色青紫的老板娘,大下巴显得越发超长。我蹲下身,把手背放在老板娘嘴上试试,还有气。
由于抢救及时,老板娘的命保住了,可药喝得太多,成了恍恍惚惚的痴呆人。
老板娘的服毒成了这个小市场的新闻,人们议论纷纷,通过“钥匙”和“熟食”的口,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老板娘的丈夫果然是个年轻有为的学者,是老板娘非常崇拜的偶像。当年他靠自学成才,是老板娘开小饭店赚钱供他到美国留学,回国后在一家研究院当研究员。可随着地位的变化,他的心也变了。首先他容不下老板娘唯一的亲人老妈。逼得老太太嫁了人,老头就是寿衣店的“死羊眼”。“死羊眼”是个不安分的花家伙,对后老伴的女儿总存非分之想。老板娘的丈夫就猜疑老婆为了钱和“死羊眼”有勾搭。那事出了以后老板娘的丈夫死也要和她离婚。绝望之下,老板娘走上绝路。
这是一出喜新厌旧的悲剧。可我纳闷,是谁那么快把那晚上的事告诉了老板娘的丈夫了呢?
4
巴黑子在瓜棚蚊帐里趴了三天。不吃不喝,瞪着眼呆呆地望着棚顶,偶尔狠狠地骂两句:“混犊子!混犊子!”
这是我认识巴黑子以来他喊得最响亮、词句最完整的一句话。我从没见到巴黑子如此愤怒过。盛怒之下,丑陋的面孔倒显出几分威武。
我不知巴黑子在骂谁,骂“死羊眼”还是老板娘。但从巴黑子的神态我看到了这个丑男人也有英俊男子同样的阳刚之气。于是我对巴黑子的印象从骨子里发生了变化。在一个阴沉的夜晚,巴黑子呜噜呜噜地向我讲述了一个令我瞠目结舌的故事。尽管巴黑子依然语无伦次,但我听一遍就懂了。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
如果不是巴黑子提起,我永远不会想到老板娘也曾是我小学的同学。巴黑子说她叫焦虹。我对这个名字已毫无印象,只模糊地记得在小学六年级下学期时我们班从外校转来一位女同学。现在已回忆不起她当时长得什么样了。
令人震惊的是,学校最丑的巴黑子竟对这小姑娘产生了刻骨铭心的感情。这个中原因不仅是焦虹长得美,关键是巴黑子和焦虹同桌相处三个月,焦虹给了他平等、热情的目光。
小学毕业了,焦虹也和我们分开了。巴黑子辍了学,到一家煤场当了送煤工。巴黑子直到眼下也没结婚,是在等着焦虹,还是因为丑找不到,弄不准。男女痴情我见得很多,但像巴黑子这样的实为罕见。
巴黑子对我说,小学毕业后他一时一刻也没忘了焦虹。他所在的煤场就负责供应焦虹家那片居民的燃煤。他说他开始只知道焦虹家住那片楼里,却不知哪个楼洞。于是他用很长时间才找到焦虹的家。
这是一大片日伪时期留下的旱楼,没有下水道,没有煤气。为了能见到焦虹,巴黑子挨家免费地把煤背到楼上。在卸煤的时候,他的耳朵早已伸进了主人房里,它在搜寻那清脆而熟悉的声音。
为这声音他整整搜寻了一年,后来他终于找到了。那时焦虹的父亲还在世,在老头颤颤微微的指引下,巴黑子把大麻袋煤背到了楼上。就在他迈进焦家门槛的当口,那熟悉的声音终于传来了,焦虹用手推着走廊门,满脸堆着少女独有的微笑。
那一刻巴黑子真是灵魂出窍了,他只扫了焦虹一眼,便把第二印象的焦虹印在脑海里。焦虹完全长成个大姑娘,比在小学的时候丰满和漂亮多了。焦虹热情地指点巴黑子把煤卸在了厨房的煤槽里,又亲自给他斟了一杯白开水。巴黑子活干得很爽快,把空麻袋往肩上一搭,呵呵地冲焦虹傻笑:“呵呵……上学没?”
焦虹让巴黑子的傻相给吓懵了,把手中的水杯往老爸手中一塞,转身进屋去了。
5
显然焦虹是没认出巴黑子。可能是因为巴黑子一身脏工作服,满脸煤灰,也可能是焦虹早就把巴黑子忘了。只三个月时间。再去掉两个半月下厂劳动,真正相处的工夫才几天,而且少年男女正是一年三变的时候认不出也是情有可原。
因为焦虹没认出巴黑子,巴黑子上了一场大火,险些丧命,在家趴了三个半月。病好之后,巴黑子本来就呜噜的说话声变得更吐字不清了。
可巴黑子对焦虹仍痴心不改。每每送煤到焦虹家那片楼,巴黑子就激动不已。如果站在她家楼下,就会觉得心跳停止了。有两三年的工夫巴黑子没再见焦虹。按时间推算焦虹一定是中学毕业了,可能到工厂上班了,也可能下乡当知青。下乡当知青的面小,巴黑子推算过,焦虹在家是独生女,很可能留城。那年快过元旦的一天,天上飘着小雪,巴黑子拉着煤车又走进焦虹家那幢楼下时,看到了立在风雪中的几只花圈。
不知是一种感觉还是什么,巴黑子的心咯噔一下,他那双埋在大眼皮下的小眼睛急速在挽联上搜寻,果然看到了一个焦字。正这当口,一身黑衣的焦虹扶着白发苍苍的老母从外面走来。着孝装的焦虹越发显得娇媚,脸色有些苍白。她和母亲的身上头上都落满了雪茶,显得几多凄凉。
她们上楼后,邻居们指着花圈议论老焦头这辈子命苦。这会儿巴黑子才知道,焦虹的老爸解放前是个蹬三轮车的,跟南市场窑子里的一个姑娘很要好。解放后窑子散了,老焦头便娶了那位姑娘,也就是现在焦虹的妈。妓女不能生育,老两口在五十岁头上在医院抱了个姑娘回来养,这就是焦虹。
知道了焦虹的身世,巴黑子更觉得焦虹可怜可爱。每到这里送煤,巴黑子总要敲开焦虹家的门,问问要不要买煤。有时焦虹来开门,没好气地回他一句:“不买!”啪地把门关上。
巴黑子咔吧两下嘴,转身下楼。显然是他第一次送煤时给焦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可巴黑子心里一点都不怪她。他不能容忍焦虹一盆一盆地从楼下往上捣动煤。为此,下次他照问不误。
真不知巴黑子有多大的耐力,他多年来就是这样地支持着。终于有一天,他的精神支柱折断了。
头三天焦老太太让巴黑子来给送煤,由于连下了三天雨,第四天一放晴巴黑子就推着煤车赶来了。真是不合时宜,巴黑子推着煤车进院时,一身婚纱的焦虹在英俊新郎的搀扶下正往轿车里钻。
巴黑子傻了,直到轿车一个劲按喇叭,他才知道煤车挡了道。
6
从此巴黑子不再到焦虹家那片送煤。煤场领导换了别人去。可当地居民总是提意见,说新来的没有巴黑子服务周到。任煤场领导怎么做工作,巴黑子死活不去,直到那片旱楼搬迁。
从此,一晃八九年巴黑子没再见到焦虹。直到有一天他偶尔到那小饭店吃饭,惊喜地发现老板娘竟是焦虹。打那以后,他几乎三天两头就来到小饭店吃饭。当然说是吃饭,不如说是吃焦虹。焦虹还是不认识他,而且连送煤人的贪婪目光都想不起来了。其实焦虹是无法想起来的,巴黑子不可能穿一身脏工作服,满脸煤灰地来吃饭。再说,这会儿小平房和旱楼差不多扒光了,巴黑子所在的煤场早散摊了。眼下巴黑子在家具城当搬运工。
在小饭店吃饭中,听到焦虹和服务小姐闲聊,巴黑子知道了焦虹同丈夫感情不合,那男人忘恩负义,总找茬要和焦虹离婚。
刚听到这信息时,巴黑子着实兴奋了好几天,他觉得自己又有希望了。可后来巴黑子就又陷入了悲痛之中,因为他看到,焦
虹对那男人爱得太深了,如果那男人抛弃她,焦虹整个人就得垮。
到这会儿,巴黑子想的和忧的不再是自己是否有希望,而是怎样能不让焦虹痛苦,不让焦虹失望。笨人自有笨人的办法,巴黑子竟闯到焦虹男人的研究所,大声向那小白脸抗议:“不能甩了她!不能!不能!”
当那小白脸弄懂了巴黑子的来意时,竟潇洒地笑了。他两手抱胸前,又一掌掌有节奏地拍着胳臂:“你是焦虹的什么人呐?”
巴黑子语塞:“我……嗯……同学。”
小白脸笑了,那笑里充满了蔑视和讥讽,显然他在为有巴黑子这个层次的同学替老婆难受。但他坚信,巴黑子绝不是焦虹的情人。因为女人是不会喜欢他的。
一瞬间,小白脸倒觉得巴黑子像印度巡捕一样,是一个很可靠的利用对象。于是他又欲擒故纵地说:“谁能看着焦虹不接触别的男人呢?如果她不同别的男人好,我可以不和她离婚。
巴黑子很激动,紫涨着脸说:“我……我看着她!”
小白脸满意地笑了,他拍了拍巴黑子的肩膀:“要保证经常向我汇报,有什么事瞒着我,我就和她离婚。”
于是巴黑子就忠于职守地当起了小白脸的护妻卫士。不用说,西瓜摊的诞生饱含了巴黑子的毕生智慧。真难为他了。
那天出了“死羊眼”夜闯小饭店的事,第二天巴黑子马上去找小白脸向他解释不是焦虹的错,是“死羊眼”不要脸。他劝小白脸千万别怪罪焦虹。
小白脸又潇洒地笑了,第二天便提出了离婚。
7
焦虹服毒后的第三天,她的老妈一股火脑出血故去了。这会焦虹正痴呆地躺在医院的病榻上,大剂量的毒液吸收,使机敏、伶俐的焦虹变成了一具植物人。
“小白脸”一次也没有到医院看望焦虹,“死羊眼”也像避瘟疫一样不再到小饭店来。焦虹的病情基本就是这样了,医院让她出院。
巴黑子的勇气这会儿大到了惊人的程度。他亲自打出租车把焦虹接回了小饭店,这个市场小巷的人们都惊诧了,被巴黑子的痴情惊诧了。连平素总爱和巴黑子取笑的“钥匙”和“熟食”也一脸敬慕地帮着巴黑子把焦虹扶进屋里。
人类是一种由情感黏合起的群体,只要你的所为被周围人认可,你就算被承认。巴黑子主动搬进小店照看焦虹,没有谁觉得不正常。店里的厨师和服务小姐自觉听从巴黑子的指挥,好像他已真正成了这个小店的主人。其实巴黑子什么也没有指挥他们,饭店仍照常营业着。
时已进秋,西瓜下去了,我们的瓜摊到了该散伙的时候,我结了帐,巴黑子把本钱拿出去,我们各赚八百元。我把自己的八百元揣起来,剩下的连本带利都递给巴黑子。巴黑子又呜噜着把我的手挡开了:“买菜、买菜,伙。”
我明白了,他是让我到小饭店来干活,担任采购。以往采购都是焦虹自己去的。反正厂里没开工,干就总比在家呆着强。我当了小饭店的采购。巴黑子的西瓜本钱又成了小饭店的流动资金。
这会的巴黑子唯一的活就是照看焦虹。焦虹的身体除了四肢还自如外,一切生活都要靠别人帮助。自打由医院出来,她几乎没说过一句话,眼圈乌青,脸部胖肿。由于药液的吸收,浑身上下一层接一层地蜕皮。
焦虹这会儿的智力按医生的说话只能达到六个月的孩子程度。给吃便吃,给喝便喝,不给便不吃不喝。大小便半失禁,且便数无常,裤裆总是湿漉漉的。
在饭店的后堂有一间小屋,焦虹和巴黑子就住在那里。可能是情感的力量,巴黑子同焦虹住在一起,没有谁怀疑他有淫荡之心。巴黑子每天大致的日程是这样的:早晨,六点起床后帮焦虹梳洗完毕,然后用倒骑驴驮着她到附近的公园晨练。焦虹什么也不懂,巴黑子替她动胳膊动腿,替她捶背按腰。这一程序要进行近一个小时,然后,巴黑子又用车把他驮回去,在饭店里吃早点,一勺勺喂他速豆浆豆腐脑,把油炸果子掰开扔进豆浆里泡着喂。
因为焦虹的胃被大量毒药烧坏了,有时吃着吃着,焦虹便哇地大吐起来。他只知道疼却不知道哪疼。巴黑子费了很长时间的猜测才摸到了症结。
8
“死羊眼”再不来光顾小饭店。“钥匙”、“熟食”倒是成了常客。每每他们过来让我陪着喝几盅。酒桌上的话题又总是离不开巴黑子。说巴黑子心好,爱得痴。他们还不知道巴黑子是从小学的时候就爱上了焦虹呢。大家共同担心的问题是万一有一天焦康复了,神志清醒后,她会接纳巴黑子吗?
说实话,我也担心这事。并非出于恶习意,我倒真希望焦虹永远这样。因为我发现这是巴黑子最幸福的阶段。
焦虹脸上身上的皮蜕了一层又一层。巴黑子一层一层精心地给她揭去,终于揭出了以往那娇若桃红的面肤。在巴黑子一个来月的精心护理下,焦虹的身体恢复得惊人。头发又有了乌黑的光泽,臃肿全部消失了,只是神志还没有完全清醒,但吃饭梳洗已能自理,大小便也不再失禁,
看着焦虹的日渐好转,大家怀着担心的喜悦。巴黑子每天总是呵呵地笑,仿佛他根本不担心有一天焦虹清醒后会怎样看他。
“小白脸”这之后来了几次,他是来看焦虹病情怎么样了,因为在神智没有完全恢复前,法院是不会判他们离婚的。
“小白脸”拍着巴黑子的肩膀说:“再努把力,有希望,我们离了婚她就是你的了。”巴黑子冲他狼一样地叫着:“呵……混蛋……!呵……混蛋!”
巴黑子一如既往,风雨无阻地用倒骑驴驮着焦虹到公园去晨练。见到人时,巴黑子不管认识不认识,一律呵呵地咧嘴笑,好像他心里有永远笑不完的内容。也是,埋在心底二十多年的情感,总算找到了喷吐口。
我老婆是个好心而爱想入非非的人,她也和大家一样担心焦虹清醒后的局面。她来到小饭店,授意我告诉巴黑子,趁焦虹还没完全清醒,生米煮成熟饭。
尽管我知道这种做法既不道德也不合法,但对巴黑子而言是不过分的。这些日子来,他和焦虹睡在一个房间,一铺小炕上,现在生米煮没煮成熟饭,谁知道呢?巴黑子也是个男人呐!
焦虹的神智越来戟清醒了,连日来,巴黑子简直成了个大孩子,走路一摇三晃的。他能不高兴吗?可终于有一天半夜,巴黑子狼一样吼叫着他和焦虹住的小屋里冲出来。
那一刻巴黑子的神态简直能吓死魔鬼,一双小眼塞满了恐怖,大下巴像吊死鬼一样耷拉着,他弓着腰,双手捂着只穿了一条短裤的羞处。
正赶上厨师和服务小姐都回家了,否则他们一定会吓死。我替他们看前店,睡在折叠床上。巴黑子就虾一样弯在我的面前呜噜呜噜地叫。
我也被他的神态吓坏了,仗着胆子往后屋挪步。那一瞬间想到是焦虹可能又自杀了。然而,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幕令人耳热心跳的场面。
秀发披肩的焦虹正坐在床上左顾右盼,内衣松散地显露出一抹酥胸。见巴黑子跟在我身后,弓着腰进来,焦虹叫着扑上去:“剑书!剑书!”
巴黑子又一声尖叫跑到门外去了。焦虹又叫着扑向:“剑书!剑书!”
我下意识地闪过身,迅速关上门,把门从外面划上。焦虹拍打着门在屋里大叫:“剑书!剑书!好狠心的剑书!”
看来焦虹是要清醒了。剑书就是那个小白脸的名字。看来,焦虹的心里还是塞满了那个剑书。我看着惊恐地缩在墙角的巴黑子,从心底替他悲哀。
在我好不容易的慰藉下,巴黑子总算安静下来,他呜噜呜噜地讲了只有我才听得懂的事情经过。
自从巴黑子和焦虹搬进了后院那小屋,两人一直睡在那铺小炕上。起初,巴黑子总是和衣而睡,而且两人之间放着药品、水杯之类的什物,一来表示分开,二来使用方便。他们的同居完全是一种情感的黏合,没有人会往淫荡上猜想。
巴黑子跟我从来不说谎。他承认,他最初挨着焦虹根本睡不着觉,不挨着又不行,夜里焦虹需要有人照顾。于是每天夜里焦睡下后,巴黑子都到外面去遛,让茫茫黑夜熄灭一个壮年男子烈烈的欲火,直到困得不行时才回屋,倒头便睡。
两个多月来,巴黑子用自己的急剧消瘦换来了焦虹的日显娇容。巴黑子那本来就“英俊”的容貌,越发令人望而生畏了。
在这其中,随着焦虹昔日娇颜的日益再现,巴黑子被欲火炙烤着的心已到了无法再自熄的程度。
这天夜里,巴黑子在外面逛了两个多小时后,回来还是难以倒头便睡。他躺在炕上,侧脸望着焦虹,那刚刚按下的欲火又腾地烧起来。他终于逾越了防线,战战兢兢爬出被窝,在熟睡的焦虹额角轻轻吻了一下。没想到焦虹突然醒来了,他用惊喜的目光看了巴黑子好一会儿,猛地把巴黑子搂住。她边叫着剑书的名字边在巴黑子身上抚摸,巴黑子惊叫地弹了起来。
9
如果说巴黑子已近不惑之年了,那么在这天之前,他充其量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是焦虹向他扑来的一瞬间他猛地长大了。
是啊,除了纯真无邪的孩童,又有谁能一爱便是二十年,且是在被爱者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可这一天突然来到时,他竟然不知所措了。再有克制力的男人,经过两个来月的耳鬓厮磨,这一瞬便是干柴烈火。然而巴黑子的这堆干柴却成了绝缘体。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非常认真地、毫无半点揶揄之意地向巴黑子讲了一个男人在此时此境可以理解的情欲冲动。怕巴黑子听不懂我的意思,我进一步深入浅出讲了生米做成熟饭的手段。
然而,出乎我的意料,巴黑子对我规劝一点即透。他像被马蜂叮了一下,猛地向后退了两步,一双小眼睛惊恐地望着我,许久,呜噜出两句话:“呵——缺德!呵——缺德!”
这一瞬间,巴黑子在我心中的印象猛地升高了。我仿佛是自己做了那缺德事,刹时间脸颊火辣辣地烫,眼睛不敢对视巴黑子那逼人的目光。可我绝不能在巴黑子面前栽跟头,狠狠地骂了句:“呆子!成不了大气候。”
尽管我用的气力很大,但那声音传到我耳鼓时,明显地底气不足。此时我不由心底生出几分担心,万一有一天焦虹醒过来,巴黑子那榆木脑袋是能做出那种事的。
自从那晚上的风波过后,巴黑子再不和焦虹睡在一个房里,这会儿的焦虹除了脑子里还有一个“小白脸”剑书的幻觉,生活基本能自理了。她见到男人就往上扑,口里喊着剑书的名字,然后便往后屋里招……
起初,被追赶的男人都惊恐地逃遁,日子久了,便不以为然了。“钥匙”和“熟食”还经常过来逗试焦虹,真真假假吓唬地占些便宜。每当这时,巴黑子都虎着脸大叫:“呵——缺德!呵——缺德!”
说来也怪,焦虹就是不把我当成剑书!可能是我常真真假假吓唬她的缘故。这样也好,否则老婆早让我鸣金收兵了。
焦虹的病情的确在好转,可她日益变得沉闷而憔悴。她不再有剑书的幻觉,但对男人均产生了排斥情绪。用笨理分析,这是一种逆反心理,由对一个男人的反感,变成对所有男人的反感。
小店里的男性都心怀危机,真不知什么时候这个老板娘勃然大怒,把所有男人都赶出去。大家并非害怕真的离开小饭店,主要是从心底对焦虹有一种责任感。如果我们真的都走了,焦虹会怎样生活。然而,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0
焦虹是先认出巴黑子的,这会儿巴黑子正在厨房里帮着把一箱啤酒往冰柜里放。焦虹坐在角落的一个椅上,瞅着瞅着焦虹的情绪就变了。她霍地扑向巴黑子,揪着他的头发往外拽,边拽边尖厉地叫道:“住手,你个丑八怪!我什么时候雇你来干活的。”
巴黑子忍着疼痛把最后一瓶啤酒放进冰柜毫不反抗,也不争辩。一副苦难深重的面孔包容了巴黑子一生的故事。
门在巴黑子身后死死地关上了。巴黑子的小行李卷被扔到门口的下水道边,菜叶和鱼鳞也趁火打劫地占据了脏兮兮的被面。巴黑子像个受了极大委屈的孩子,粗糙而黑涩的腮撇出两道肉楞子,两颗硕大的泪珠,在沟沟坎坎上艰难地爬。
正巧我买菜回来,这一幕全看在眼里。我实在受不了啦,气愤地敲着门。
巴黑子拦腰把我抱着,拼死命把我扯到一起,冲我呜噜着什么,我懂他的意思。到这个时候,他还护着他的焦虹。
我的心简直都要炸开了,这哪是男人?造物主为何弄出这等残次品?我拼命扭过身,左右开弓,给了巴黑子两个大嘴巴。
巴黑子被我打愣了,捂着脸呆呆地望着我。我顾不得他的情绪,回身一脚把小饭店的门踹开,指着焦虹的鼻子大骂:“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娘们,他是你的大恩人!他默默地爱了你二十几年。没有他你早就死了。你这样对待他丧尽天良!”
焦虹好像完全清醒。我的叫骂令她大怒不止。她一脚把反弹回来的门又踹开“滚出去!两个臭卖西瓜,想占我的便宜?找错门了!我是被那臭男人甩了,可也轮不到你们来捡破烂。滚!快滚!不滚我报告派出所啦!”
一时间,我像掉进了冰窖里,两个多月来积蓄的热情骤然凝成了冰疙瘩。我痴痴地退出了小饭店。
“钥匙”和“熟食”赶来向焦虹解释。焦虹店门紧闭,不加理会。
我像做了一场大梦,几经折腾,终于醒来了,除了一身的疲惫,再没有任何收获。巴黑子凑到了我的面前,苦着脸冲我呜噜:“呵——走!呵——走吧。”
看着那张天生苦相,可恨又可怜的脸,我真想再他几个耳光。可我终于没忍下手,把狠狠举起的手轻轻地拍在他的后背上:“走吧,咱们走吧!别总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过些日子帮你找个心眼好、和你般配的。世上女人没死光。”
说来也怪,以往做梦都梦不到巴黑子,从打这一段的朝夕相处,竟令我总是放心不下他。
我们分手后,我仍是几张报纸一缸茶地打发日子。每每咀嚼茶根时,便会想到和巴黑子共同生活的那段日子,也和茶叶一样,苦森森地却有些回味。转眼进了晚秋。一天,巴黑子兴奋地来到我家。
11
我简直被巴黑子的情绪感染了。我从没见过巴黑子这等羞涩过。他进屋来便没头没脑地说:“呵——喜酒!呵——喜酒!全去!”
说罢,巴黑子像个怕羞的大姑娘,落荒而逃。
我老婆和孩子都被弄怔了,还, 以为巴黑子得了精神病。
老婆说:“咳,好好的人给弄成这样!单相思可真害人呐!”她又对孩子说:“往后他一个人来千万别给他开门,当心他打你。”
我说:“胡扯,巴黑子那哪是疯了,他是要结婚了。”
老婆眼睛瞪得灯泡似的:“结婚?谁嫁给他!”
是呀,谁嫁给他呢?我又想,谁嫁给他谁享福。
巴黑子扔下一句话就跑了,他在哪办喜事?新娘是谁?我一概不知。
后来我找到“钥匙”和“熟食”。他们竟然告诉我,新娘是焦虹,并向我讲了巴黑子和焦虹后来的事。
他俩说:巴黑子几次去剑书的单位乞求剑书和焦虹重归于好。他告诉剑书,焦虹的病已经全好了,上次和“寿衣”了,可情况却不按巴黑子的意图发展,焦虹主动跟剑书办了离婚手续。经过大磨大难, ,焦虹成熟了,剑书解脱了。

诗赋绽芳蕊 今来觅知音
版权所有:诗赋网 Copyright 2008-2016 zgshifu.com All Rights Reserved 辽ICP备18006388号
诗赋杂志投稿邮箱:sunwulang@163.com
联系人:轻盈 QQ:418193847、1969288009、466968777 QQ群号(点击链接) 电话:15609834167 E-mail:sttsty@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