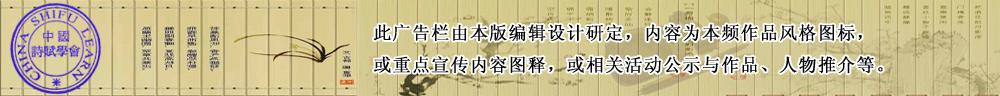
- 胜者为王【057】婶婶... [庄河教师]
- 【柳判传奇】̶... [羽砚]
- 美丽的逃亡(少年勿点)... [烽火]
- 17·天伦孽【草稿】... [羽砚]
- 我是你的稻草人... [皓月]
- 胜者为王【024】三个... [庄河教师]
- 31集电视和谐文学连续... [韦志远]
- 韦志远扶贫... [韦志远]
- 男奴(一)... [卡萨布兰]
- 恩施剿匪记 (二)解放... [云木欣欣]
灵 魂 偷 渡
第 二 章
大渔船渐渐远去了,海面又复平静。我们的船却热闹起来。哑巴咳木雕般在舵舱里开着船。昆沙腆胸迭肚地站在甲板上。我趾高气昂地蹲在他脚边。这是我们的基本战斗队形。
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七男五女,十二个蓬头垢面的偷渡客。
船一徐徐开动,海风便不再闷热。我喜欢开船,讨厌停下来。昆沙绅士而威严地凝视着他们,足有五分钟,这是他的杀威棒。我知道下面昆沙就要让我开始工作了。每当昆沙威严凝视的时侯,我便开始对每一个偷渡客进行安检。辨别和记住他们的味道,弄清简单行囊中的物件,搜出任何武器和能造成危害的凶器。
每当这时,我发现偷渡客们便异常恐慌,我便在他们的惊恐中,盯住他们的眼睛;透过他们的眼睛,我能读懂他们的心事,甚至过去的故事。所以,昆沙命他们都摘下墨镜。可此时,他们都低眉顺眼,不敢正视我,令我无法知道他们昨天的故事。好在此时我没有必要去读懂他们昨天的故事,尽管狗也和人类一样,有窥探别人隐私的癖好。我只要完成昆沙的第一指令,找出他们身上不该出现的东西,并记住他们每一个人的特征就算完成任务,就能获得几块牛肉干。
我是昆沙的扫描仪,是他的海关。任何细微的隐匿都休想从我鼻子底下溜过。于是我脑海底片中就折射出了下列的印象:
一个五十多岁有些尖顶的男人,昆沙给他的代号叫尖顶。尖顶身边站着一个白胖的十五六岁的女孩,时尚的服饰已经凌乱不堪,昆沙给她的代号叫松花。松花怕狗,见了我,惊恐地尖叫着,偎进尖顶怀里。松花喊尖顶舅舅。
松花的身边是个四十来岁、端装秀丽、气质极佳的女人,我从她身上嗅到了书香的味道,昆沙给她的代号叫校长。
校长脚边的甲板上,坐着个三十七八岁的戴着金丝边眼镜的文质彬彬的男人,昆沙给他的代号叫医生。我在他身上闻到了药水的味道。这会儿医生正吱牙裂嘴地抱着自己的脚作痛苦状,可能是走山路他的双脚都打了泡,这会儿让海水一蜇,疼痛难忍。我感到他有些歇斯底里。
医生的旁边是个五十来岁的细高男人,他干瘦的身板挺拔、枯槁,一身干部服,脏兮兮的看不出颜色。他头上那顶制服帽庄严而滑稽,像某个小品演员。他一脸严肃地背着手,可随着船的晃动,又不得不时而把手松开,去扶身边的人。我虽然看不清他的眼睛,却能感觉到他该是个不算小,也不算大的官员。对人类的官职我素来概念模糊,弄不懂他是什么科级、厅级还是什么处级之类的狗屁官,反正是个官。他总是往下拉帽檐,怕被海风刮掉。于是昆沙给他的代号叫老帽。
老帽身边是个很帅的小伙子,他似乎跟老帽很熟。老帽每要倒时,总去扶他。挺帅的小伙二十八九岁的样子,健壮,俊朗,严肃,挺直,像当过兵。我不大懂人类的审美观,不知道他够不够帅哥,反正他的严肃着实令我感到一丝敬畏。昆沙给他的代号叫良子。我不解为啥叫他良子,可能昆沙认为他是个好小伙。良子身边站着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俊秀的女孩儿,都二十二三岁的模样,我知道在人类这叫双胞胎。虽然长得一样美,气质却很是不同,一个泼辣外向,一个文质羞怯。在我们犬类一胎五、六个兄弟姐妹很是正常事,可人类就有些惊奇。人类很难分辨出双胞胎之间的差别,在我们的眼中却一目了然。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昆沙给她们的代号一个叫大梅子,一个叫小梅子。可能生活在南方的昆沙更喜欢北方的梅花。
挨着大梅子和小梅子的是三个男孩,大的十八九岁的样子,中的十六七岁的样子,小的十四五岁的样子。
大的两颊落腮胡子,干枯的黄发,长脸,不会笑,说话声低沉而不清,像在喉咙里塞了只鸟蛋。他的容貌显老,比实际年龄要大许多。他好像是搞体育的,一身壮硕的肌肉,胸脯和我们犬类一样长着黑毛,黑毛间又撒满了青春痘痘。于是昆沙叫他胡子。
十六七岁的男孩样子很冷酷,小帅哥样的那种,像电视剧里的许文强。他人很文静,眼睛里却透出一股与年龄极不相附的睿智和老成,时而还会闪露出几丝狡黠和凶狠。我似乎感觉出这个男孩不简单。昆沙叫他文强。
十四五岁的男孩长得白白净净,稍显瘦弱,像个女孩,个子也不高,人很激灵,又活泼。他是上船后惟一无恐惧感的人。他问昆沙,渡一条“蛇”赚多少钱。昆沙就拍着他的头说他是个小犹太。于是他的代号就叫小犹子。
蛇头从不问偷渡客的真实姓名,上船后给每个人起个代号,一路上就都相互叫代号。昆沙的眼睛绝毒,基本一眼就能看出偷渡客的身份,不差多少。为此,他给起的代号常常惊人的贴切。最后一个也是个女人,三十来岁的模样。她身上有一股妖气。我想昆沙也感觉到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属于美丽的那种,属于也是妖艳。她似乎对狗没有恐惧,还伸手抚摸了我的头。我从她手上闻到了一股怪怪的味道,那是一种能令我嗅觉麻痹失灵的味道。我怕她给我施什么魔法,机警地躲开了她的再一次抚摸,远远地盯着她看。她开始冲我朗朗而鬼异地笑,于是我认定她是个女巫。昆沙果然叫她女巫。
第一道程序过后,我又开始围着甲板上的一堆行李扫描,寻找我们这条道上不该携带的东西。昆沙常说,鼠有鼠道,蛇有蛇道,在偷渡的水道上绝不能有水儿啊,粉儿之类的毒品出现,这是道上的规矩。因为官方打击贩毒,远比打击偷渡要严厉得多。昆沙做的是长久生意。
我在一大堆行李中,除了闻到了美金和金条的味道,其它均不存在。我冲主人吠了两声,报告工作结束。昆沙很满意,上前一步,冲大家一挥手,开始讲话。
“很好!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到昆沙号,我是船长昆沙,也是未来三十六小时中你们的主人。”昆沙的声音仍然很绅士。我看到偷渡客们情绪有些不对。
“什么话?我们是交了钱的,不是你的奴隶!”尖顶说。
“对不起各位,我知道,能从蛇道上出走的,都非等闲之辈。但无论你是哪个山头的老大,还是达官显贵,来到我的船上都是我的货。安全接货,顺利运货是我的天职。之所以说我是你们的主人,起码在这三十六个小时之内你们是我的货。我可不希望货在我的船上有啥闪失。配合吧!”昆沙话语平淡,却不容置辩。“好吧,我们开始了。请诸位拿回自己的行李。每人向我交两千美金。注意,是美金,而不是日元之类的其它狗屁货币,只要美金,只要两千美金,先生们、女士们!”
人群骚动了,尖顶又道:“我们可是交过一大笔钱的,咋又要交钱?”
医生附和:“公海上也乱收费吗?”
“先生们、女士们,请听我说,我只再说一遍,请听好了:我先收的那是买路钱,现在要收的是头道杵(登船费),在诸位离开我船的时候还要收二道杵(下船费)。诸位弄懂了吗?”
“这不是乱收费是什么!”医生忿然,“最初的蛇头说拿到一笔钱就会送我们到地儿,可一路上我们一次次被卖,一次交冤枉钱!你告诉我们,还要交几次钱才能到达目的地?”
“先生,头次走蛇道吧?外行啦!哪有一杆子杵到底的活!我这个昆沙,既不是金三角的那个大毒枭坤沙,又不是海盗亨利·摩根。走粉儿、化霜(贩毒)的杵门子(来钱道)我不干,翻窝子(盗墓、倒卖文物)的杵门子咱不粘。马六甲海峡上兄弟漂了二十几年,这黄金蛇道可都是用真金白银铺就的。海上条子(警察)、亨利·摩根(海盗)哪个不是吞金角子活命的!还有,兄弟们一路的吃喝钱、造船钱、修船钱。兄弟剩下的只是零主碎琴(小钱)。望各位见谅,见谅!不是兄弟敲竹杠,走上蛇道的朋友,哪个不是在脱离苦海,奔向光明?兄弟为大家搭桥铺路,诸位一旦闯进自由世界,火穴大转(挣了大钱),就会知道当年兄弟只是要了你们几个零主碎琴(小钱)。到时恨不能寻我再报呢!咋样各位,上头道杵吧?只两千美金!”
“也太黑了点吧?两千美金,又是一万六千多块人民币,你要打我们土豪哇!”尖顶脸痛苦得扭曲。
“砸砸浆(压压价)?”良子上前拍了一下昆沙的肩膀。
昆沙眼一诧:“道上兄弟?”拱了拱拳,“更该懂行规了!进娼门、走蛇道,听说过打折砸浆的?台湾竹连帮老大许海清、澳门十四K 崩牙驹、合肥的胡斌、河南的宋留根、广州的周光龙、越南的张文甘、香港张子强,这些老大可都在我的船上走过货,没见人砸过浆。交够枸迷杵(银子),我保各位顺风顺水转货。要是哪位老大觉得价不公,我给倒杵子(找回买路钱),立马让猎鲨送他下船。”说罢,瞥了我一眼。
我挺了挺腰板。每当这时我都十分自豪,感到自己是真正的勇士,更感到了自我价值。偷渡客们再没人敢多说话。昆沙又一脸和气地接着说:“这位老大就别砸浆了。”
一直没吭声的老帽挺了挺腰板,把双手背到后面,船一晃,他一趔趄,胳膊又搭在了良子的肩膀上,可另一只手又背在身后,字正腔圆地问:“谁都要交吗?”
“是的,老大!”昆沙说。
“你知道我是谁吗?”老帽接着问。
昆沙不屑地转过身去,背对着老帽:“不知道,老大。不过,不管你是官是匪,是人是妖,上了我的船,可就是我的货。二十多年蛇道上漂着,各类鸟兽我见多了!官官匪匪,人人妖妖,谁分得清?不恭了!”昆沙猛转身,把一对“黑橄榄”贴在老帽鼻子尖上,阴着嗓子问,“谁知你是个啥子东西?”
老帽气得要发作,良子拍了拍他的肩膀。
“各位快请吧!”昆沙接着说,“半小时后这里将有巡逻艇经过,不想漏舱掉底就快点!”
我看到偷渡客们陆续不情愿地打开行李,把两千美金分别交到昆沙手中。我不知道两千美金是个什么概念,但我讨厌钱,我看到他们给钱的样子,就想起我的第一主人把我出卖给昆沙时的样子,很是厌恶。
“好,很好!有了这头道杵,就是在我的船上买了保险;踏上了昆沙号,你们就等于向自由世界踏进了一条腿,我将竭诚为您服务。好吧,下面过来领食品,是免费的,一人一份。”昆沙指着甲板上堆放着的几个食品箱,“每人两瓶三百五十毫升的矿泉水,方便面或面包自选,每人两包。”
“两千美金就两瓶水?太黑啦!主食少一些还行,水是不能少的,脱了水人会有生命危险!”医生一脸职业神圣。
“这位先生的话好极了!人是万万缺不了水的。在我这条船上有充足的水和食物,够大家享用两个月的,有水果、罐头、香烟,还有白酒和上好的路易十三等洋酒。不过这些不再免费,需要美元消费。三百五十毫升矿泉水三百美元一瓶,方便面一百美元一包,其他的食品上面都标有标签,大家可以自由选购。”
“天价呀?”医生忿然。
“不贵!不贵!这就是世界末日的价格,这就是通往天堂的地狱之票。买吧!买吧!”女巫两手指向苍天狂叫,“过来吧,大家过来分享造物主最后留给我们的食物吧!”
女巫的狂叫令偷渡客们厌恶而恐怖,好在大家已习惯了她的存在,没人理会。众人绕过她,围住了两个大食品箱,去拿属于自己的那份免费食物。
昆沙得意地扫了众人一眼,从食品箱中拿过一个面包,撕成几块抛向大海。不知这是一种什么仪式还是善举,昆沙每当此时都会这样做。我心抽紧了。瞬间,一直跟着船盘旋的一群海鸟扑向海面,抢食面包。几只抢到面包的海鸟叼着食物拔向高空,可瞬间,又如同几块石头坠落海水。海鸟们挣扎几下后,在海面死去。
偷渡客们手捧食物惊诧了。
“食有剧毒!是氰酸甲铝还是砒霜?不然不能死得这么快!”医生惊恐道。
“您很在行,先生。”昆沙狰狞地笑着,“我是在教训一下这些讨厌的海鸟。大家尽可放心食用,不是所有食物都含有剧毒。只要大家遵守船上的规矩,按价索购,保大家安全。如果有谁抢食或偷食,就爱莫能助了。大家领的食物保证是没毒的。”说着,昆沙又从食品箱中拿起一个面包,咬了一口,“绝对没毒!大家下舱吧。”
偷渡客们战惊惊地看着手中的食物,不知所措。
“钻了十几天的山沟子,又蹲了五天黑船舱,眼睛都要瞎了。刚才那个船老大说,到了公海我们就不用再蹲黑船舱了。”尖顶说着,一屁股坐在甲板上。
“就让我们呆在甲板上吧。都要闷死了!”医生说,“你看我的脚,爬山弄得血肉模糊,又在船舱里焐了几天,都已经发炎了,如果得了败血症,我会死的。你要赔偿!”
“哦——”昆沙走到医生身边,抓过他的脚,“真是可怜!我的货呀,怪可怜!猎鲨,帮帮他。”
我知道主人的意思,扑过去,叼住医生的衣服,眨眼间拖过甲板把他扔进海里。医生来不及尖叫,便球一样在海水中一起一伏。昆沙瞬间又扯过一张鱼网,向医生撒去。眨眼,医生如一条甲鱼,滚落进网里。昆沙迅速提起鱼网,把纲绳绑在船尾的锚绳上。医生就这样被缠在网里,挂在船边,露出头,身子在海水中被船拖着缓缓前行。
医生在水中惊叫:“快拽我上来!快拽我上来!我会被鲨鱼吃掉的!”
昆沙不理采,对众人说:“我保他三十六小时内不会得败血症。谁还有什么要求吗?”
我看到其余的十一个人均惊恐得不再敢吱声。尖顶拉着外甥女松花马上堆着笑脸对昆沙道:“我们绝对服从船长指挥,船舱怎么走?”
昆沙说:“很好!猎鲨,带他们去船舱。各位拿好自己的行李,看好美金和金条,贵重物品丢失,本船概不负责。希望大家乖乖地呆在船舱里,不要出声。这里虽是公海,可也是哼利·摩根(海盗)们的天下。我昆沙在蛇道上漂了二十几年,还没折过货,各位配合吧!”
“等一等!”校长说。
“喔,这位女士还有要求?”昆沙很有礼貌。
“把他拉上来吧,他会死的。马六甲海峡有鲨鱼,我知道。”校长说。
“哦——那各位的意思呢?”昆沙绅士地冲大家摊着手。
我看到他们都惊诧地望着昆沙,没人敢应答。
昆沙很得意:“O K !”
他来到船边,提着纲绳,把医生悠上甲板。
医生浑身颤抖着爬出鱼网,像一只刚打捞上来的老鳖。
“诸位请吧!”昆沙再次躬腰摊手。
“等一等!”大梅子冲过来,冲昆沙歇斯底里地狂叫,“把我也扔进海里吧?快呀!我认可干干净净地死去,也再不想脏兮兮地活着了。身上都要生蛆了,我要洗澡。我必须洗澡!都半个多月没洗脸、洗澡了。不然我就跳进海里,毁了你的货,让你赚不到我的钱!”
“船长,让我们也洗洗吧?再不洗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活着了。”校长说。
看着几个女人的乞求,昆沙无奈地摊开双手:“真是麻烦!女人真是麻烦!”
昆沙来到桅杆下,打开一个开关,同时冲大家喊到:“十五分钟,只能洗十五分钟。”
瞬间,清澈的海水从一支胶管中喷出。小梅子扑过去,大梅子扑过去,校长扑过去;女人们扑过去后,男人们也都跟着扑了过去。他们疯狂地撕扯着自己的衣服,疯狂地在清澈的海水淋浴下清洗着。
我看到一群近乎赤裸的男女们,尽情地让海水荡涤着满身污垢。我看到下午炽热的阳光,在水亮的黄白色的皮肤上跳舞。我还看到湿漉漉的长发被海风抚动,女人们变得滋润鲜亮,男人们也不再肮脏。我不懂这是不是人类的美,但我感觉他们的轮廓和形象变得清晰可人。
这时数女巫最狂放,她只脱得剩了三个点,边甩动着一头长发,边颤动着肥硕的双乳,双手指向苍天用沙哑的嗓子叫着:“洗吧!洗吧!洗去污垢,洗去灰尘,干干净净地迎接世界末日的到来!山崩海啸,天塌地陷,这个世界将不复存在,我们将升入天堂,得到永生!”
女巫的狂笑使我感到了一丝不安。我今天本来就感到不安,不知为什么。我看到昆沙也显出从未有过的烦躁,他高声喊着:“好了,好了,十五分钟到了,到十五分钟了!”可偷渡客们仍陶醉在清澈的海水浴中,没人理会他。
远远一条巡逻船向我们开来,船上挂着什么国的旗子我永远搞不懂,但能看出那是一条官船。昆沙掏出手枪冲天空放了一枪,偷渡客们沉默了、定格了。
“原地蹲下,谁也不许多话!”昆沙厉声道。
转眼间官船驶到了我们的船边,放慢速度,却没靠过来。
“打鱼呢,昆沙?”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冲我们喊。
昆沙老椰子样的脑壳堆满了笑:“您好哇,船长?您要的椰子油给您带来了。”
昆沙把一个塑料瓶抛向船长。我知道那塑料瓶中是两根金
条。
船长接过塑料瓶,冲昆沙摆摆手:“一路顺风!小心啊,前面还有鲨鱼!”
官船开走了。
顿时,昆沙的满脸笑容变成狰狞:“洗吧!洗吧!妈的,洗没了我两根金条!快,都给我滚到舱里去!”
突然,一直在船边玩耍的小犹子惊叫起来:“鱼,快看,这么多鱼!这鱼好怪,有大尾巴的,还有嘴里吐着泡的。看,还有眼睛出血的。它们都要死了,这是怎么回事?”
校长惊慌地扑到船边:“咋这么多死鱼?这是叉齿鱼、巨喉鱼,长嘴的是鞭吻鱼。这些可都是深水鱼呀,咋都浮水面上来了?不好,要海啸!”她扑回甲板,拉住昆沙的手,“船长,快靠岸,要海啸!这些都是深水鱼,只有海下地震、海底温度升高,它们才浮到海面上来。一定是要海啸。快,我们赶快靠岸!请相信我,我是学生物的!”
“胡说八道!没坐过船吗?在船上是不能胡说八道的!快,都给我滚到舱里去!”
校长不管不顾地仍然大喊:“相信我!这是真的!赶快靠岸吧,晚了就来不及了!快,向那个小岛子靠!”
“再胡说我把你扔海里去!那是什么岛?是鬼子礁!船会撞碎的,你要找死吗!猎鲨,快把他们赶下舱去!”
我遵从主人之命,冲偷渡客们狂叫起来。转瞬间把他们赶下船舱。昆沙哐地把船舱门上了把大锁。我听到从船舱门里传来咚、咚的敲打声和男女的厮叫声。望着海面的死鱼,我越发烦躁不安起来,似乎感觉真的要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我把自己扁扁地贴在甲板上。我听到了大海深处的隆隆声,像驶来的千军万马。我还嗅到了来自大海深处的一种味道,像是硫磺味。不好,我感觉到大海确实要出事,可我没经历过,不知道要出什么事。我冲昆沙狂吠,告诉他我的感受。
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永远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居然又冲我大骂:“你个杂种,跟着叫什么?也告诉我要海啸吗?你个笨蛋,这回你错啦!我漂了半辈子海,比你懂!”
我真的无法跟他沟通,这个愚蠢的笨家伙!我把他又塞进我嘴里的牛肉干狠狠地吐出去,再趴在船边看海。这时,我看到海水已经像开锅一样冒泡、翻滚。昆沙似乎也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他扯着嗓子向舵舱中的哑巴咳喊着:“快,右舵四十五,全速!哑巴,听到了吗?鬼子礁!”
哑巴咳大声地连续咳、咳地把船向鬼子礁开去。
此时海水已沸腾,小船像一片枯叶,被海水悠来荡去。我和昆沙都扁扁地吸在船甲板上,咸热的海水不时从我们身上冲刷而过,像有人倒提大海给我们洗澡。
危急中,我灵魂出壳,飘向半空。果然,我看到整个海都像一盆倾倒的水,立了起来,船变成一粒黑枣核,在水中旋转着起起伏伏。鬼子礁就在船边,却无岸可靠。突然,一个更大的浪推来,我们的船被推到浪尖……我的灵魂被海水打湿,只得立即归壳。瞬间便失去了知觉。

诗赋绽芳蕊 今来觅知音
版权所有:诗赋网 Copyright 2008-2016 zgshifu.com All Rights Reserved 辽ICP备18006388号
诗赋杂志投稿邮箱:sunwulang@163.com
联系人:轻盈 QQ:418193847、1969288009、466968777 QQ群号(点击链接) 电话:15609834167 E-mail:sttsty@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