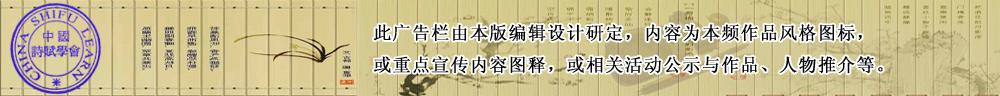
- 胜者为王【057】婶婶... [庄河教师]
- 【柳判传奇】̶... [羽砚]
- 美丽的逃亡(少年勿点)... [烽火]
- 17·天伦孽【草稿】... [羽砚]
- 我是你的稻草人... [皓月]
- 胜者为王【024】三个... [庄河教师]
- 31集电视和谐文学连续... [韦志远]
- 韦志远扶贫... [韦志远]
- 男奴(一)... [卡萨布兰]
- 恩施剿匪记 (二)解放... [云木欣欣]
我的《家园》三部曲后记
后 记
欲写《家园》三部曲的念头由来已久。早在二十三年前,从大连教育学院语言文学系毕业分配在庄河县高级中学教书时,骑着自行车来往于歇马山的褶皱与县城的大街之间(那时庄河还没有撤县设市),我就有了要写一部这样的大书的想法。几欲提笔,都因思想意识过于低下,文学修养远远不够,力不从心而搁浅了。
但,搁置不等于放弃。那时我二十九岁,我计划五十几岁时把它完成。也就是说,《家园》耗费了我二十三年的心血。构思了二十年,写了三年。现在,名字叫做《家园》的妈妈生下了三胞胎,老大叫《鸟语》,老二叫《水刀》,老三叫《龟裂》。也许在你的心目中,这三个臭小子长得很丑陋。不过,猫养猫亲,狗养狗亲。哪怕这三个臭小子是脑瘫儿,他们的老妈《家园》喜欢;我也喜欢,我是他们的老爸。他们是我的儿子,尽管他们丑陋得长着猪尾巴棍。
为了生养他们,我准备了二十年。
二十年来,我当然也没闲着,除了搞新闻的本质工作外,还出了十三本散文集。这十三个臭小子长得还算漂亮,只可惜他们连脑瘫儿还不如,他们根本就没长脑子。漂亮女孩没长脑子行,因为可以当花瓶摆着好看。漂亮男孩就不可饶恕了,因为他们必将一无是处。因此,我在这里庄严宣告:我从此与我那十三个漂亮的脑瘫儿脱离父子关系。希望他们给我滚得远远的,最好马上在地球上消失算了。或许我这个当老子的过于苛刻,毕竟他们都是生长在“听命”与“应景”的时代,也怪不得他们。孩子残疾恰恰就是老子无能。可见,我还是罪责难逃。话又说回来了,也不能说我这十三个臭小子真的就一无是处,至少我在他们身上练习了语言,提高了书面语言的表达能力。你看,事物就怕辩证地看待。一辩证,“一无是处”的东西竟有了益处。尽管在哲学上我让一分为二害惨了,在文学上我让现实主义害苦了,动辄却要去辩证一下。
我说我的十三本散文集没有什么思想性,这是千真万确。当然,他们也不是空穴来风。为了生育他们,我不得不广泛地接触社会现实。我老家那地方还是很有特点的,可以说是山河沸腾,田园优美。庄河,庄河,庄庄有河。有的村庄甚至都有几条河,而山里更是溪流纵横。辽南最著名的三条大河都在庄河,从东到西分布着英那河水系,庄河水系,碧流河水系,每条大河都建有水库,通过管网连成一体,养育着大连市五百余万人口,还要灌溉着万顷商品粮基地。辽南的前三座高峰都在庄河。依次为步云山、歇马山、龙华山。这三大山系统领了一座座连绵不断的山峦,每座山都美得像诗。你听那名字吧,荷花山,光明山,蓉花山,三架山,鞍子山,观驾山,小孤山,平山,尖山,城山,石山,鸡冠山。传说薛礼征东,一步一个云朵翻越了步云山,又在歇马山上歇过马。这两座山由此而得名。龙华山顶有天然的般若洞,明朝宏真法师在洞中建庙,香火共云朵萦绕于顶峰。著名的辽南小桂林冰峪沟就在龙华山系。无论阳光四射,云卷云舒;还是风起云涌,天雨潇潇;一步入庄河大地,都会领略到山河壮丽,人马萧萧的万千气象。
整日里恬静着的就是田园。村屯里没有整齐划一的街道,二三十户人家集中在一条沟里,房后有高高的风水树,房前有长长的流水。房后栽桑房前种柳,年年过来年年有。这是植树的民俗。院落里倒是有些热闹,却都是动物们的。鸡多鸭少鹅子只有三两只。圈里都有一两头克郎猪,养着杀年猪啖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的小伙子长得都很帅气,大姑娘长得都很水灵。无论男女老幼,穿戴打扮得都很时尚,只是一张口说话就觉得土气得掉渣了。这里汉族、满族、蒙古族、锡伯族混居。所有的少数民族早已被汉族同化了,他们说着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听懂的辽南土话。满、蒙、锡后裔大都不知道自己的本来民族语言了。每每改朝换代,他们为了免于灭门之灾,都谎报为汉族。他们大都聚族而居在大营子、巴尔虎营子、夏营子和土城子一带。这些县志上都有记载。而那些满、蒙、锡后裔却并不知内情。园子里种有青葱、白菜、辣椒、茄子、黄瓜、西红柿、葫芦、南瓜、春不老和水芹菜等。割一把带露的嫩韭炒鸡蛋,秀声可餐。再捏上二两高粱烧,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大田里种的是苞米、大豆、高粱、谷子、花生和地瓜。成片的稻田都水改旱了,水库大坝加高截流,供城里用水,水田就灌不上了。土地承包,改革开放,山村里只剩下上岁数的老年人耕烟播雨,中青年都外出上学与打工了。田园里幽静得像一幅幅优美的山水画。偶有老人赶着黄牛哞哞地从田头渠畔走过,你会误认为那是从一轴画卷里步出的仙人呢。分田分牲口那会儿,我和我的未婚妻放假回家,曾夜以继日地为生产队里的社员写承包合同。一晃三十余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仿佛如昨,清晰可见。当然,也少不了为民的鸡争狗斗,尔诈吾虞;作恶的男盗女娼,奸淫妇女,杀人放火;为官的贪污受贿,打击报复,草菅人命。这些残酷而丑恶的社会现实比比皆是,现在回想起来历历在目,只是我不想展开来叙述。我生怕它玷污了我这篇单纯的《后记》。
正是这些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相互纠缠与纷争,从而点燃了我要书写我的《家园》的欲望。如果所有的思想和主义都无从考证它的对与错,那么,至少我们应当学会辨别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或许就是我最初要写这部《家园》的动因了。
这些大抵可以算得上我在社会生活方面的准备。
为了表达的需要,二十年来,我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名著。我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届中师生,读的就是中文系。其实,我是被录取在英语系的,只因对汉语言创作的痴迷,改学了中文系。在庄河北部山区教了两年语文,重新参加成人高考,又上教育学院读了四年语言文学系。我读了六年中外名著。在教学之余,我踌躇满志地提笔要描述我的《家园》时,大脑里却一片空白。我知道还是我的功底不足。只有不断地拼命地充实与弥补自己,才能鼓足底气。别无他路。我又精读了二十年我喜欢的中外名著。曹雪芹的半部《红楼梦》,我几乎能熟读成诵。鲁迅的《阿Q正传》,我可以倒背如流。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和《诉讼》,普鲁斯特的《追亿似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等等,都使我爱不释手。当然,我也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我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我读霍布斯鲍姆的《极端年代》,我读尼采的《查拉斯图特拉》,我读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我还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读书让我从郁闷走向郁闷,从孤独走向孤独。郁闷和孤独走到了极处,我心豁然。
下面,我告诉你我最喜欢的几位我心目中大师级的大家(我不用作家这个称谓,因为他们决不仅仅是作家)。
我最喜欢曹雪芹。他一生只写了唯一的半部书,却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绝对的经典。中国古典小说的四大名著中其它三部虽说都是完整的精品,但和半部《红楼梦》比就相形见绌了。他的创作态度是极其令人称道的。决无功利,不求发表,只在知己的文友圈传阅与传抄,他却坚信自己的作品将是文学史上的丰碑。用毛笔书写着蝇头小楷,“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从而把作品锤炼到“一字不可更,一句不可改”的地步,终于成就了半部“一字一血珠”的精典。他却过着“一技无成,半生潦倒”,“蓬牖茅椽,绳床瓦灶”的苦日子,最终“书未尽而芹先死”。现在看来,它百科全书式的博大精深,它挖掘不尽的主题意蕴,它个性鲜明的人物塑造,它现实主义与超自然手法的完美结合,它纯洁的母语运用与白描技巧,统统都是汉语文学的师范。《红楼梦》里没有“什么阶级斗争”,连主仆的争斗也没有,顶多是焦大喝醉了骂两句脏话。但反映的却是“社会制度的级端稳定性与个人生存的极其无常性”,和谐的外表装饰了尖锐的矛盾,整个社会机体自上而下的生存危机。曹雪芹和他所描述的四大家族就是这种生存危机的牺牲品。这是一个永恒的存在,难道现在不也是这样吗?
我最喜欢普鲁斯特。他有点像曹雪芹,一生只写了一部大书《追亿似水流年》。所不同的是,他终于完成这部举世闻名的精典之作。他也是一生不图功利,不求发表,只为传世。他二十岁准备写书,三十五岁动笔,五十一岁去世,这部二百四十万字的巨著终于完成。他一生带着严重的哮喘痼疾,为一部书而矢志不渝,终于圆满著就,令我钦佩。他教我明白了我们是生活在时间的波涛里的人,而时光是可以重现的。他教我明白了“真正的天堂是我们失去了天堂”。他教我明白了“一个生性敏感却缺乏想像力的人同样能写出令人拍案叫绝的好小说”。他教我明白了小说是人类生活有血有肉的切片。他教我明白了小说完全可以委婉细腻、幽深曲折成一条时间的河,人就是这河里的鱼。
我最爱卡夫卡。在他短短的四十年的生命旅程中,他只发表了为数可怜的几个短篇。他不是不想发表,而是没有人能读懂他。三十岁到四十岁是他创作的顶峰,先后写了三个未完成的长篇:《美国》、《审判》与《城堡》。肺病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既然不能发表,他就在遗嘱里告诉他的挚友马克斯·布罗德把他的作品焚之一炬。好在他的挚友背叛了他,不但没有烧毁,还全部整理出版了。从此,欧美文坛上前五名的大师级人物诞生了。他的短篇小说《变形记》就是卡夫卡风格的同义语。他是存在主义文学的先驱,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表现主义文学的先驱,他是现代主义文学之父。异化、恐惧、焦虑、荒谬和无能充斥他的作品的字里行间。他是一位现代思想家。他的不朽在于他提出的诸多的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答案。他塑造的文学形象甲虫格里高尔,足可以和“超一流”文学形象哈姆雷特、唐吉诃德比肩。我喜欢他善良、正直、真诚、不通世故。我喜欢他是一个失去庇护的在穿着衣服的人群中惊慌失措的“唯一的裸体者”。我喜欢他以痛苦走进世界,以绝望拥抱爱人,以惊恐触摸真相,以毁灭为自己加冕的人生方式。我喜欢他是一个终生都在从事创作的并不在乎主流社会承认与否的现代主义文学之父。我喜欢他是一个苦行的圣徒、一个可怜的单身汉、一个犹豫不定的彷徨者、一个有着心理缺陷的微不足道的好人。或许我就是一个“精神赤裸者”,所以我爱他。顺便说一句,每每提起卡夫卡,我就想起了印象派绘画大帅梵高,我觉得他俩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的人生与创作经历又是何其相似乃尔。
我最喜欢乔伊斯。他是“意识流”小说和一种崭新文体的开创者。现代文学如果没有他“将像现代物理学没有爱因斯坦一样不可思议”。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一百本小说”中,他的《尤利西斯》高居榜首。世界学术界有专门研究他的杂志。他是一位与时俱进的文学大师。他的创作有一个从现实主义走向现代主义又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过程。从《都柏林人》到《艺术家青年时期的画像》再到《尤利西斯》终到《芬尼根守灵夜》就是这样一个清晰的进程。我喜欢他那股子破坏传统、颠覆秩序、解构现实的劲头。我喜欢他以弗洛伊德主义为出发点对人类内心世界进行深入而广泛的挖掘。我喜欢他为小说创作开辟了崭新的途径,为后世树立了典范。我是那样地羡慕勇于并且善于创新的文学大师。
我最喜欢鲁迅。像他这样的大家竟然敢于只用一个中篇而立于中国现代文学之首。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阿Q正传》,那么也便没有了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这和只以半个长篇而立足文史的曹雪芹同样伟大。他又和阿根廷大作家博尔赫斯相像,一生只著有短篇而没有长篇,却并不影响他成为世界级大文豪。鲁迅创作的文学形象阿Q也并不亚于唐吉诃德的份量。阿Q的精神胜利法,欧美发达国家的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同样存在。大凡地球村人都受着精神胜利法的制约。然而,在鲁迅先生的笔下,还远不止这些。他讨论国民性,为国人寻找出路,寻求希望。《阿Q正传》绝对不是像已有定评说的那样,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即脱离了人民群众。试想,像阿Q这样把革命看成要什么有什么,爱谁是谁的流氓无产者,能领导革命成功吗?即使成功了,他又能领导人民实现现代化吗?先生在这里只是提出问题也就足够了,引发人们思考也便是最终目的了。很多问题一旦有了答案,接踵而来的便是教条,便是迷信了。这正是我从先生的作品中之所学。
我的最爱还有好多,因为时间关系不再一一赘述了。
这些也大抵可以算得上我在阅读方面的准备。
任何一个问题可能比一千个答案更具有实际意义。科学教育我永远不停止地去寻找那只明知不存在的白乌鸦。哲学又教诲我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枉下结论。一切主义都是只能起捆绑作用的绳索。像牛顿这样的物理学家,发现了惯性与万有引力定律的同时,也回答不了“宇宙是原来就有的”还是“无中生有的”?他用物理推导的最终结论是:宇宙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就是那只并不存在的白乌鸦。这就是科学。我们找到了那只白乌鸦也便找到了上帝也便找到了宇宙的起源也便找到了人类的起源。可是,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这么胡乱地寻找下去吗?人活着到底要干点什么?人活着就是为了死吗?那么干吗还要活着呢?我回答不上来的时候,我想到了写小说。
我也曾思考过我的写作目的。我觉得我活得特别迷惘,特别惶惑,特别孤寂,我便想到了写小说。我也在报刊上发过几个短篇,都是唯美而悲观的小东西,一是为了哗众取宠,二是为了赚取稿费,承载不了我多少思想,于是我想到了写长篇。哪怕无处发表,无人理睬,我也在所不辞。我坚定不移地相信我的存在。人活着很可能就是要像曹雪芹、卡夫卡、普鲁思特、乔伊斯、鲁迅、梵高、高更等人一样,用自己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王小波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目的时,说他就和登山家一样,因为山在他面前,他必须把它踩在脚下。我没有这种洒脱,也没有这种征服欲。我的写作,实在是因为内心的痛苦、寂寞、孤独、恐惧、郁闷和无助而不得不提起笔来往稿纸上倾诉(我从不用电脑写作)。显而易见,我做了个赔本的买卖,我的书赔大了。但我愿意这么干。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我是我写作故我在,写作的过程就是证明我存在的过程。
有评论家说,为人要做到真善美,核心是一个真。真达到了,自然也就善了美了。而多少伟人偏偏就倒在这个真上。做人作文务求一个真,不管你用了几多主流主义不愿意认同的新手法,真实永放光芒。譬如曹雪芹,卡夫卡就是求真的化身。这就是我力求的目标,无论做人作文只求真实。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主流社会,主流意识,主流文化不承认你的真实。如果不用“阶级,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亡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来的文明史”的观点看问题的话,主流社会都是从末流、中流、次流社会爬上去的。因此过不了多久,主流社会里的一些腐化堕落的腐败分子就显出了他虚假的嘴脸。这些腐败分子恰恰就是像阿Q一样的铁杆贫雇农出身,他们一旦得势了比谁都坏,比如刘青山,比如辽宁的慕、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资产阶级队伍中,就没有真善美的典范吗?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就没有假恶丑的存在吗?像割韭菜一样越割越旺的腐败分子不正是假恶丑的典型吗?所以说,真实根本不用主流社会承认,后人自有评说。这使我想起了中国朦胧诗群崛起时,所谓的主流评论家们对年青的诗人的责难:看不懂还叫诗吗?青年诗人们的回答是:我的儿子会懂的。有趣的是,还都等他们的儿子出世,朦胧诗就作为中国新诗不可逾越的巅峰而崛起了。我在这架天衣无缝的统治机器面前,恐惧得瑟瑟发抖,但是我一点都不惧怕我的《家园》惨遭冷遇,因为它是真实的。眼下被主流社会恩宠的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被历史遗忘得一干二净。历史往往在非主流文化遗迹中寻找真实,譬如曹雪芹的半部《红楼梦》所预见和概括的封建社会的衰亡,再譬如卡夫卡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对人性的异化的预见。我的《家园》只求真实,不求承认。我恐惧于社会的承认,它往住是对真实的作品死刑的宣判。我恐惧得发抖是有理由的。
这些也大抵可以算得上我在心理方面的准备。
在动笔以前,我翻来覆去地思考我的叙述风格问题。我羡慕鲁斯特的委婉细腻,几近于絮絮叨叨地描述一个只作一句白描就可以凸现的细节的语言风格;我也羡慕卡夫卡那种空灵、飘忽、悬疑的语言风格;我还羡慕乔伊斯任由意识流淌,完全自主写作的语言风格。我研读中国当代作家很有影响的代表作。我欣赏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与《未来世界》,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唤》,他们都把欧化汉语做到了极致。我也欣赏贾平凹的古典白描,苏童的唯美的叙述。东西的率性,邱华栋的自主,林白的原生态,格非的悬疑,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我直接的语言风格启迪的则是李洱的《花腔》,张承志的《金牧场》,莫言的《酒国》,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受活》和《坚硬如水》。他们让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母语写作和现代叙述。
我不想套用曹雪芹和贾平凹的白描,我也不想采用王小波和余华的欧化,我爱上了阎连科的白话母语与现代性的结合。当然不是照搬硬套,我坚守了我的辽南方言母语。我发挥了我的快人快语的率性。这是符合我的性格特点的表达方式,我写起来便得心应手。
这些也大抵可以算得上我在叙述风格方面的准备。
我崇尚蒙田、孟德斯鸠、普鲁思特等大家对人生的安排。五十岁以前周游世界,认识社会,体验人生;博览群书,积累知识。五十岁以后深居简出,闭门著述。四十六岁那年(二00三年三月一日),我从某报社副总编的位置上办理了内退,准备回家著述。调整了两年,我重读了卡夫卡、普鲁斯特和乔伊斯。二00五年一月十七日,我终于动笔了。我写得时快时慢,快时一天能随笔淌出上万字,缓时三天还写不出一行字。一年一部,越写越厚,现在这个《家园》三部曲总算画上了句号。只是还不知道是否圆满,再说了,我压根就讨厌圆满。我很崇尚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观,只要主题的深刻、问题的尖锐和个性的突出,是不求人物塑造的完美和情节的错综的。我要的是倾诉的快感和不完美之美。
小说是绝对个性化的东西。它和诗歌一样都是古老的语言艺术。而欧语系、拉丁语系、阿拉伯语系和东方语系等都有登峰造极的建树。尽管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边缘文化大爆炸的时代,但只要人类语言不消失,它就有存在的理由。因此,我们不仅要坚守它,而且还要发展它。我们有理由比我们我前辈走得更远。也许小说只是个艺术形式,个性的充分展示却是实在的内核。没有个性就没有存在。我力求以自我的个性特征一直往前走。也许我是穿着别人的鞋,却要走自己的路。是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打的去吧!
在我写累了的时候,我就反复阅读高行健获得二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灵山》。它是朋友从香港给我捎来的,可见香港回归了真好。还有当代文学评论家张学昕先生陪我喝酒聊天。通读他的文字,我读出了真诚,读到了侠义。他的文论点亮了我孤寂的灵魂。我在赠他书的扉页上写下这样一句话:钓雨耕烟于无中生有,说文解字以虚处为实。
《家园》三部曲出齐了后,我准备再调整两年,就着手写一部一直到死才能完成的大书。要么就像《追亿似水年华》那样长,要么就像《阿Q正传》那样短,要么就像《红楼梦》那样只写一半,要么就像卡夫卡那样写完了在遗嘱里让朋友烧掉……高度和谐的社会和极其无常的生活,使我无法预料命运会怎样摆布我的余生,也许我明天就会死去。危机就掩蔽在时间的波涛里,恐怖分分秒秒都在觊觎着我的生命。我把我的生命预支给上帝好了。
构思了二十年,写了三年,这个丑陋的三胞胎总算问世了。探讨来探讨去,我还是不知道我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你知道吗?你要是知道,我这就跟你走,因为我一无所有……
最令人恐惧的还在时间,不等我们选好了目的地,它就用无形锯齿牙把我们的肌体一块一块地咬死掉了,最终夺去了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家园真的就在上帝手里吗?我们如果能以光的速度飞行,我们便跳出了时间的吞噬了吗?上帝为什么不来拯救我们呢?在修改《龟裂》的余暇,我细细研读了奥尔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他说,灵魂栖息于四界:(一)子宫;(二)人世间;(三)我们现在所在的婆娑,或中间界;(四)审判之后将要前往的天堂或地狱。只有当一个人脱离了时空的牢笼,他才会明白生命是一件束衣。一个没有躯体的灵魂在亡者的国度享受无比欢愉。同样,人世间最大的幸福就是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躯体。这就是我要苦苦寻找的精神家园的归宿吗?
我想起了我一生最喜欢做的三件事:运动、读书和做爱。运动使我体魄强健,读书让我灵魂充实;那么做爱呢?那真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它使我热爱生命,拥抱苦难。性爱恰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存活形式,那么母语的原生态原来竟然是生命的本质。我没有理由放弃生命赋予我抒写它的权利和义务。奥尔罕·帕慕克说:“安抚爱情的最佳途径,不正是做爱吗?”
我用贝克特《等待戈多》的结尾开篇,我用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的开篇结尾——
如今我已是一个死人,成了一具躺在井底的死尸。
荐自:作家沙里途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dlcamel

诗赋绽芳蕊 今来觅知音
版权所有:诗赋网 Copyright 2008-2016 zgshifu.com All Rights Reserved 辽ICP备18006388号
诗赋杂志投稿邮箱:sunwulang@163.com
联系人:轻盈 QQ:418193847、1969288009、466968777 QQ群号(点击链接) 电话:15609834167 E-mail:sttsty@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