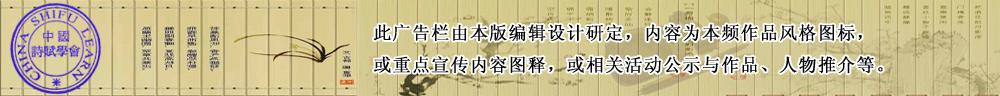
- 高原之魂 ——王芳散... [雨晴]
- 学诗之法... [青青子佩]
- 杂谈... [初生牛犊]
- 心底飞歌 ——诗人王跃... [雨晴]
- 实践确实是检验真理的唯... [江湖夜雨]
- 靡靡相思苦,阵阵刀割痛... [翰林院士]
- 《诗论》修改稿... [崔思军]
- 关于《临洞庭上张丞相》... [秋水孤帆]
- 学格律诗28问答... [秋水孤帆]
- 《赋写风华》贺序... [诗赋家王]
- 中国历史上十大骈文高手... [周晓明]
- 诗歌概论... [覃应海]
- 艺术含蓄学(全本)... [郭有生]
- 古代离情诗诗译书画意境... [王铁&n]
- 怎样写七言绝句... [风霜雪雨]
- 生命的珍果 思想的明珠... [晓雪(著]
- 平水韵表中没收入的汉字... [淘淘一笑]
- 艺术含蓄学... [郭有生]
- 扬东北诗风,创“黑土”... [程奎]
- 《大家一起来写赋》... [石涵]
生命的绝响
——读《名人的遗书》有感
一
何为生命的绝响?她可是一个生命最后的灿烂?她可是生命过程中最为眩目的光华?她可是一个生命在长时间的聚光之后瞬间所爆发的最后的灵光?无疑这些平庸的语言都难以概括她全部内涵与意义。浅白的文字也许就是——“最后的话”可以狭义的加以说明。但这最后的话却是生与死的表达,它是艺术与哲学之桥,是人与神的会晤。于是生命的绝响就有了非凡的意义,解读和聆听这些绝响,无疑是一条探究生命本源的绝好的路径。直抵本真,荡去虚枉,灵魂的敞开是如此的坦诚,那些大气的沉郁的勇敢的柔情的灵魂如喷薄而出的红日,义薄云天气吞山河。在天地之间敞开自己,敞开生命企悟,敞开折断的翅膀,用自剖的方式敞开我们的本真、人的本真。
绝响之音虽有长有短有弱有强,乃至有大有小有清有浊,但它们大都是令人扼腕的难以忘怀的。聆听绝响,对后继者来说的确是灵魂的洗礼,震憾与顿悟,惊叹与共鸣,缅怀与崇敬,深思与觉醒……都会油然而生。为铮铮铁骨所动,为大气飞扬的灵魂而汗颜,为生命的强音而颤抖,为大义凛然而豁然开朗。沉醉其中,有了登高望远的情怀,感动在这个有些麻木的世界里就有了特殊的意义。这些真之声,美之花,善之果又怎不令人感动?肃然起敬的也许不是这些在天籁大音之下的微响,而是生命之花在凋谢前的凄美与悲壮,这凄美与悲壮包含了更多的整体的意义——人类的意义,文明的意义。一句“死之静美”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啊!
常人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诚哉斯言,善就是真就是美,而至大则包容天地,涵盖千情万物,惟大才可心昭天日情动寰宇。惟美才能感召众生而天长地久,化育万物而魅力无穷。生命的绝响本身就赋予了她的至真至大至善至美,面对这样的精神遗产,谁又能说她不是生命的特质吸纳了文明所爆发的灵光?这些优秀的个体谁又不是情连古今,思接千载、心系万物、神驰宇宙、智通神灵的娇娇者?!在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绝响是“即兴”不出的,更与作秀相去十万八千里。
圣哲苏格拉底在临终前也说出了另类善言——“人在将死之际,通常就成了先知。”这是哲人对生命和世界的穿透。知难,知己难知客难,先知更难。绝响且能迸发先知,不能不说是不幸中的万幸。说它不幸是因为绝响都是将死之言,悲惜是应有的常态,说幸是因为绝响之所以是绝响就于它是难得的精神财富。这些感天地泣鬼神的强音在喧嚣与红尘之中依然在天地间盘旋、盘旋,在心存宁静者的心间荡漾。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在信仰缺失、精神萎缩、大道蒙尘、文化被更多的非文化取代的今天,绝响作为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就有了更为特殊的价值与意义。虽说绝响是以个体的形式喷吐或吟唱而出的,但他(她)仍然是我们派去敲响神祗之门的信使,是人类之音融于天簌之音的必然。
至今我还记得奶奶说的最后一句话——“我真舍不得你们!”我心领神会,这里的“你们”就是她认知的世界和生活。八十多年的艰辛历程,就这么一句姑且称之为绝响的话,表达了她对生命的眷恋,对美的不舍。父亲在弥留之际已没力气写字和说话,但他那最后的一瞥,对我却是铭心刻骨的,真是无声胜有声啊!而立之年的我似乎懂得了比千言万语更为悠长更为苍劲的话语。父亲最后的嘱咐令我不敢忘怀,殷殷之情一直激励着我去直面人生,去积极向善,淡定从容地宁静自我,应对外物。
人是符号。对那些能触动灵魂的符号我总是心生敬畏的。绝响也是符号,而且是特殊状态下的符号。解读和领悟,发现与缅怀,冷峭之中有生命的亲切袭来,为能在那片片磷火中发现一些钙、铁、磷的痕迹,为我还有更多的人提供了醒目的参照,索性就把这只业已尘封的匣子打开,让那些鲜活的灵魂再昭日月,让他们的风彩再放光辉,这不仅是最好的纪念和缅怀,更为重要的是为我们走向未来找到了一杆杆高高的坐标,这无疑是先辈的幸事,也是我们自己的幸事。
二
简索历史人物,总有挥之不去的情节在缠绕着我,让我的灵魂驻足在他们的大义和细节之中。对革命者的林觉民我所知甚少,只知道他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至于他的《与妻书》过去也仅仅是似懂非懂的看过节选。直到读了南帆的《辛亥年的枪声》,我才知道林觉民不仅是个“以身殉天下”的义士,更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才子,一个懂得爱情的情圣。在文字之中,有幸结识这位历史人物真是有缘。庆幸之余,萦绕于怀的是这位集侠士、革命者、才子、情圣于一体的人依然是个谜,明知死神在彼却依然勇往直前,直观的诉诸是这样:一面是义无反顾地走向弹雨之巷,一面落笔生花:“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一个径直就义而又情意绵绵的伟岸之躯、之灵向我们走来,灵肉俱大,捍外秀中,行如飓风,静如处子,刚柔并济,阴阳双飞,对这样的生命你能简单的枉称“思齐”?“思”或许可以远游可以驰骋,但“齐”就不那么容易了。正因为这样,他才是个谜。用信仰、用革命理论乃至狂热来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你用“天下尽殉”、“其殉一也”依然贬损了这个生命的价值,甚至是对死的亵渎;你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来套、来附会都不那么令人、令自己诚服,能够宽慰自我的是他“死的光荣”——林觉民不仅当之无愧,似乎也更能贴近他的本真。
如果说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林觉民是以慷慨悲歌之士定格于历史星空,那么他的才情更足以使他的生命放射出久远的光芒,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者的林觉民就其影响的深远而言,一定不如文化者兼情圣的林觉民,假若他囿于述而不作,不给我们留下《秉父书》和《与妻书》,那么他短促的生命就不会如此丰盈,壮怀激烈的他就会缺少大气磅礴的文化韵味,他的精神遗产就不会如此的精致,如此的耐人寻味。
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才是统率才是灵魂。
三
南帆这样描述林觉民——“豪气干云、一诺千金;仰天悲歌,击鼓笑骂;一剑封喉,血溅五步——这是林觉民的形象。”与林觉民相比,瞿秋白所缺少的正是那么一股任侠之气,更没有革命狂热者那种“只要主义真,掉头不要紧”的英雄气。《多余的话》给了我们这样浅直的印象,但细细揣测,在他那绵绵的诉说中依然有强大的气流在拽着你赶着你走向1935年5月17日的汀州监狱,一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开场白,把我们引入另类绝响的语境之中,坦白、率直、真诚,一个身体虚弱的白面书生在那里自白,他要告诉这个世界,历史选错了他,他也有负自己的党团,他的身体不是什么特殊材料构成的,所以他没有铁肩可担什么“道义”;他的灵魂似乎是空空荡荡的,是什么“主义”也使他坚挺不了的,他只是一个书生,想读书、想教书、想写书,仅此而已。
在政治是统率是灵魂的时代,在纷乱不堪的年月里,谁也由不得你自己做主,都是浪中沙。作为一个党团的主要领导人,在有些迷茫的前提下,无所适从,更无作为,成绩没有,败绩频频,你不是软弱无能又是什么?若从单纯的政治角度,这样的定论并没有冤枉谁。但问题的要害却在于,瞿秋白最后还是献身了,还是英勇就义了。虽说“叛徒”是洗涮掉了,但烈士头衔却是不能说给就给的。这大概也符合瞿秋白自己的意思。他并不十分信仰什么,所以就无所谓“叛徒”;他本就不想为什么而献身,所以烈士名号的期待对他而言可以说无。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面好些人还以为我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永久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如此坦诚,也是需要勇气的。站在本党本团体的立场上,怒其不争——“你怎么能这样说!”可能会成为主流意见。这意见本身并没有错,但问题的要害就在于,对一个政治上没有什么兴趣,身居要职却没有什么立场的人而言,你捧杀与棒杀都有些不着边际,甚至找错了对象。在《历史的误会》这章里,瞿秋白有这样的话:“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毋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更为关键的是,他既没有豪言壮语,要誓死捍卫什么主义,更没有向另类主义或其他党团表忠心,乞求放他一条生路,以图苟且偷生。他没有这样,正因为如此,他才超越了党团和主义,作为政治人物,从政治角度去看,这确是有些不合适宜,甚至有失风范。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人文而不是政治角度来看,“多余的话”不仅不是多余,而且是必需说的,起码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理解不同于宽宥。放在一个更为宏大的参照系里,一些是非就会模糊起来,而且也不再那么绝对。对瞿秋白其人其文的解读,更应该这样,用宏阔的眼光去看,要兼顾他的社会背景,“误会”历程,以及他的脆弱或特质,只有这样,才能接近历史的本真,人的本真。
这么说并没有什么消极倾向和其他用意,只是想换一个角度来看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与此同时要说明的是瞿秋白是人不是神,他的缺点和错误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历史的误会”这节最后他写道:“我写这些话,决不是要脱卸什么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负什么责任,我决不推脱,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历史“误会”了他,党团错误地选择了瞿秋白,但他也有负党团,更“误会”了历史,虽然他的“取独秀而代之”有很多违心的成分,但大浪毕竟把你推到了那个位置,你就不能既瞻前顾后无所作为,又狠不下心主动请辞,这样做,心愿或许是好的,但客观上却给组织造成了损失,你既不完全信仰这个主义又不另谋他途,在风云变幻的时局里没有主张,随波逐流,丧失斗志得过且过,这哪里还是一个党的领袖人物?这分明是“混世魔王”嘛,若按非此即彼的逻辑推论,瞿秋白不仅是一个不合格的革命者,就连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恐怕也是不够格的。因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是这个时代的良心和批判者。作为一个主要领导人,对自己党团的前途悲观失望,对社会现实看水流舟,漠视历史沉浮,甘当局外人,不愿或不敢去面对腥风血雨的现实,更不用说去改造世界,这样的政治人物不退出历史舞台那才是历史的误会。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依然让人揪心,即使在七十余年后的今天,你很难做到“批判”一通就心安理得,“同情”一番就万事大吉,“悲惜”一阵就淡出感觉了。如果是这样,你仍有遥隔而疏远的感觉,无名的痛阵阵袭来,驱赶不了的是他的真实他难以名状的亲和力。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回避和绕开都显得多余,更没有必要。
在诸如我这样的凡夫俗子者的心中,瞿秋白依然是一尊奇特的参照,他虽然不是慷慨悲歌之士,不是赤肝裂胆的大侠,更不是怒发冲冠式的英雄,但他的真实足以让那些为虚枉而献身的所谓英雄好汉,乃至速朽的伟人矮将下去,他的情他的思是那么的绵长,悠远之中你能看到一个灵魂的挣扎和喘息,而这正是那些被另类历史误会而成功了的人所不能比拟的。我想,瞿秋白的魅力就在于此,敞开自己的脆弱和难言之隐,诚实而不失生动的给历史给后人作个交待,除却政治因素,可以解读可以亲近可以缅怀他生与死的过程,以及他那羸弱躯壳里所流淌的绝非黯淡的情思。我曾一厢情愿的假设,倘若他被开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历史能宽容于他,国民党不杀他这个徒有虚名的共产党员,能够让他活着,两党都将他遗忘,让他干自己有兴趣的事,我相信他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的卡夫卡,那么,现代中国文化大观园就会多一枝奇葩,甚至可能为我们奉献一位世界级文化大师。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政治是冷酷的。命运不可能由你自己主宰。大浪淘沙,红尘滚滚,我们都是这滔滔江河中被泥沙裹挟的微粒。时势造英雄,时势更弄人,误会了的不仅仅是那些名见经传的显赫人物,更多的奇异之士也深埋其中,从这个角度去说,“天生我才必有用”也只不过是那些有发言权有发言机会的人的自励而已。
瞿秋白在《脆弱的二元人物》这节里为自己画了像:“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他一直渴望“甜蜜的”休息,期待自己“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在他很是直观的诉求里,我们看到了什么?一具疲惫的灵肉厌烦了风风火火,直想休息,不愿再染指身外的事事物物,对纷争更是避之不及,甚至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也不愿多想了,至于那些看似崇高的东西更是懒得继续下去了,这是纯碎的颓废吗?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但从深层去看未必全是负面的。因为不理世事不涉万物本身就是一种选择,正确与否关键要看当时的背景条件,即便是错也是不愿再担什么道义再负党团责任的错,至于这道义与责任本身是亲近了好还是疏远了好,仍然要因人而异,都不好一言定生死。本来应该就人而论人的,但他又是个政治人物,自然绕不开政治,又因政治太过复杂,在此就不枉作评论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瞿秋白在厌倦的背后,是有心灵自由之向往的,他愈是想“停止”一切思想,他的向往就愈是迫切。对党团而言,一个领导人物有如此的精神面貌,的确是有负这个党团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对一个理性的人而言,打退堂鼓的想法也并非就罪大恶极,不可宽恕。人和事都具有多面性,有人愿意为集体奉献一切,其勇气可嘉,更无可指责,只要不到“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也没什么不好;反之,一个不愿再在这个集体中混下去了,要另辟他途,要重新开始,但他绝不出卖这个集体,绝不以牺牲别人为前提,这样的人,谁能说他就是叛徒就是坏蛋。对一个集团而言,如果进得出不得,那只能说这个集体是偏狭的,不文明的。因为它限制了人的自由。这是从人文角度而不是从政治角度来说的,人文有人文的天地,政治有政治的规则。历史既然“误会”了他,难道他不能把这个“误会”交换给历史吗?
站在曾经信仰或者有所信仰的立场上,瞿秋白还是有所交待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思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原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地位。沦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至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的实在些,是废物。
瞧,这自我剖析一点也不掖掖藏藏,并看不出有什么开脱“罪责”的意思。一个希望早点结束生命的人,不管是来自精神压力的,还是源于健康因素的,他有必要绞尽脑汁来欺骗世人吗?人到这个时候本真是要占上峰的,那些虚枉的东西往往会不打自跑。因此,所谓的“纲”和“线”在行将就木者眼中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在瞿秋白的文字中,似乎能够领略到“忏悔”的气息,但他决不是为了讨好哪家党团,更不是别出心裁的作秀,他仅仅是在忧郁的叙说中间表明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款款之中有些吃力,我们清晰的看到一个心神惧疲、灵肉不支的生命在用最后的话说出他自己的真实,这大概也是他惟一能做的。因为是历史的误会造就了他,那他就有责任把误会澄清,至于有没有人买帐,能不能经得住同志们的推敲,他才懒得管它,或者说已无力顾及也许更为恰当。但这与犯混和无赖是有天壤之别的。
从历史的深处走来,一具连镣烤也戴不起了的灵肉,他的自白虽然显得过余绵软轻柔、有气无力。乍看,似乎有失一个党团领袖的风范,但仔细品味之后,你会发现一切强加的不是之词都显得不合适宜,都有些隔靴搔痒,而他的本真虽说没有多少力气,更缺少那点“牛劲”,但那些偏狭之气在它面前依然不攻自破。我惊异于这样柔弱的自白,它感动人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它凭什么穿越了那么阴暗的时空?事过境迁之后依然让人揪心,依然让人唏嘘不已。这么缠绵的文字怎抵得上诸如“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那么铿锵有力的绝响呢?但我依然认为,掷地有声的绝响自然是个好的,但它彰显的更多的是气度,而思想的内涵,有时是与气势不成比例的,这里决没有半点为“弱者”辩护的意思,相反对诸如谭嗣同、陈天华、林觉民这样豪气干云的激狭之士我是万分敬仰的,而像瞿秋白这样十足的书生,真正被历史的误会卷入时代旋涡的人,他的诀别之言依然是绝响,聆听其声还是有身临其境的感动。历史的误会已成定局,个人的命运不会重来,悲悯和亲近是因了文化的同根同脉,亲切的是思想的亲切是人的亲切。倘若去掉曾经鲜活楚楚的人,我们在历史的隧洞里只谈政治壁垒和信仰差异,依然在“阵营“的习惯思维中打漩,那么我们就会既有愧于先人,又有愧于文化,这是我们必须警惕加反省的。一个载负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知识分子,就这么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他带着罪恶的结核,带着沉重的镣烤走向生命的终结。但他决不是简单的而来,又简单的而去,在生与死之间的确有“历史的误会”,当然也有他自身的脆弱——思想的、身体的等等。他既有些厌世又有些留恋,他的坦白看似柔弱无力,但它仍然令许多人汗颜。因为他坦白的对象不是自己曾身在其中的党团,更不是向敌对党团的检讨,而是向天下,向所有的人坦白他的历程和情思,这是超越了政治信仰的,无疑也是对历史负责的表现。正因为如此,他的话虽有气无力,但又的确是耐人寻味的。一个透明的人,一颗散开的心,一段真实的人生,一粒宇宙间的微尘,他来到了这个尘世,他思过他想过,他甚至力所能及的做过——这已足够。
走了一圈又回到原点上。他是文人,他最后的文字是向人推荐可读之书;他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他最后的留恋是中国豆腐。
这就是他的真实,瞿秋白最不能让人忘怀的就是他的真实。
四
苏格拉底在信仰和法律都背叛或舍弃不了的二难中,选择了死亡。对他而言,这是拒绝堕落的最佳方式,也是他忠于国家和法律,坚持信仰和真理的必理归宿。
他在临终前的演讲中说:“逃避死亡并不难,要避免堕落才是难的,因它跑得比死要快。”作为哲学家的苏格拉底,他洞悉到了死亡的奥秘,那份坦荡是常人难以抵达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是死亡催生了他的先知——国家的走向人的发展在他心中已有了一个明晰的脉络,他的理想和预见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得到了相当的应证。作为教育家的苏格拉底,他的选择无疑是一种引导和示范,既然他已打通了人与神的通道,那他就索性敞开这幽幽的神祗之道,让人们在认识自我、放飞心灵、激发美德,创造未来的过程中能有一个醒目的参照。这种作为这种胸怀不是那些被神化了的“大圣先师”可以比拟的,“要尊敬死,才能满怀希望。”大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践行了他的诺言。他的那些在广场上与民众的对话,他的哲学语境以及他最后的实践,都充分表达了他对生命的敬畏,也惟其如此,才可能自然地展现他的平等思想,他的意义就在于他来自民间,他的哲学是生活的哲学——大众的哲学。仅此一点,他就高于和优于许多后来者了。哲学家乃至官员如果能有真切的平民意识,能站在大众的立场上去思想去行为,这种感情这种倾向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他的生命力也远比那些纯粹的哲学家或政治家要强大要恒久不知多少倍。
亲切的苏格拉底在最后的演讲中还原了人的亲切,他说“如果我的儿子们长大后,置财富或其他事情于美德之外的话,法官们,处罚他们吧!使他们痛苦,就像我使你们痛苦一样。如果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其实胸中根本无物时,责备他们,就像我责备你们一样。如果他们没有做应该做的事,同样地责罚他们吧!”一个哲学家留给我们最后的话竟是如此地平实,没有慷慨激昂之词,没有气吞山河之势,仿佛就像一个农夫爷爷在弥留之际嘱咐自己的儿孙如何耕田如何勤俭如何做人一样,只是想把自己的人生经验、思想所得告诉后人,仅此而已。
不拖泥带水,不端圣哲的架子,不说那些深奥难懂的话,亲切而朴实,直白而深邃——大师的风彩就这样印在了人们的脑海里。
五
政治人物的功过是非一如政治本身一样,都不好简单地判定。政治家的遗言同样不好解读,当然,像刘备托孤之类的话不在此列。更多的政治人物在最后的话中大都有这样几层意思:人事安排,典型的是中国帝王的诏书;未了之志的设想,政治是为了改造社会,起势之初,纲领、目标是少不了的,天不作美,未尽之业总得有个交待;表情达意,因有遗憾,为激励来者,鼓舞斗志,豪言壮语,情沛而理直,杰作佳句不乏其例,煽情作秀气势逼人。但时过境迁再看这些政治性杰作,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不是很多。
拿破仑的遗书据说是他用了八天时间才写就的,他的圣赫勒拿岛上,僵卧在床上,病残的躯身,心灵的折磨,其痛其苦是可以想象的。有人称他的这份遗书是政治性的杰作,是他一生最出色的文件,评价甚高。但令我奇怪的是,拿破仑的这份遗书用了相当的文字来安排他留下的钱财,共计约六百万法郎,分到最多的是蒙托隆,他得到了二百万法郎,其他人得了五十至两万五千法郎,这是拿破仑用来奖赏那些对他忠心耿耿并做出了牺牲的人,这些人总共得到了三百肆拾万法郎,而饱受战争苦难的布里埃纳市和梅里市各得到一百万法郎,其他地区和官兵得到了约六十万法郎。
我们无法猜度拿破仑在最后书写时的心情,但我们却很明了他那六百万法郎的去向,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如此看重他的身外之物的归宿呢?是内疚,是无奈的补偿,是最后的收买人心?我看都是但又不完全是。但不管怎么说,遣散这些钱财总比留给家人要好,起码能解决一些人的生活困境,作为一个被流放的人,能够补偿他人的,除了心灵就只有钱财了。也就是说他做了他认为自己该做的事,无愧天地无愧人心,此愿足矣!虽是两手空空,但能轻松而去,不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吗?
这个细节说明拿破仑并不是目无一切的,他能知微见著,体恤将士,散尽钱财,其人情味十足可见一斑。做个大夫丈不难,难得的是能把英雄气与真性情融为一体的人,或许这才是他感动人的地方。
拿破仑的遗书可圈可点之外甚多,比如他的预见:“消除封建残余,保证人的尊严,促进经济繁荣,以稳定的联邦形式统一欧洲。”一百七十多年后的“欧洲共同体”是不是他心中的联邦?我不得而知,但他依然洞见了欧洲的未来,这是了不起的。
六
所谓“复杂的人”大抵是因为他身上集中了很多矛盾的东西,曹操是这样,曾国藩是这样,所有够得上“人物”的人,都是这样,他们大都是复杂的人。这里的复杂主要是指矛盾的集合,若把“矛盾”一对对地拆开了,复杂的人也就简单了。
在品读“绝响”的符号中,有一个人我觉得是省略不掉的,他就是被人誉为“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最后一尊精神偶像”的曾国藩。为什么说不能省略了他,是他在文学、思想史上的地位所决定的,在如雨如云的中国古代作家中,前无古人,独占鳌头的要算曾国藩的家书了,数量逾千,内容广泛,论文论学,论修身论成德都不失为一部生活宝鉴。这样的“人物”你能随便省略吗?这不仅是有无政治标签的问题,而是尊不尊重思想文化的问题。
1870年7月,曾国藩在接手处理“天津教案”时写了一份遗嘱,是给两个儿子的。
余生平略涉先儒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可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欲将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功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
将修身之法归结为“忮、求”二字,真可谓先博而后精,厚积而薄发。娓娓道来,真实而细密,平常而又深入,此等良言自是庸常之辈做作不了的,对于一个一生都未曾放弃自己的品德修养,停止过反省与自责的人而言,这篇《示子》真不愧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实写照。
就是这样一个写出“善莫大可恕,德莫凶于妒”,“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的人,给我们留下千余封家书的人怎么能和“曾剃头”联系在一起?他分明就是孔子转世,朱子再生嘛,其诲人不倦,为人导师的形象不是早就跃然纸上了吗?这大概就是人们把他冠以“复杂的人”的原因吧。但不管怎么说,以“修身之道”作为思想基础,以不忮不求作为为人准则的人,总不至于被全盘否定,被说得一无是处吧?!更何况,曾文正公所仰仗的文化是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而他的反哺依然是对传统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这有什么不好?特别是在文化价值混乱不堪、传统被一而再、再而三割裂的今天,读这样的文字不啻为一副清凉剂,既有益于传统文化的链接,又有助于浮躁者的心安,按人生境界说,惟有心安方可理得,静心既是一种功夫又是一种境界,应当成为知识者的生活常态。
曾国藩真正的遗书应该是另外一份遗嘱,通篇依然是“忮”“求”的细化,可以看出这份遗书比《示子》的书写要从容几分。开篇就是:“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清心而后寡欲,进而达到无欲则安、则刚的目的,这“老生常谈”缘于欲望粒子的顽强,缘于外物的诱惑林林总总。人生在世与外物的遭遇势所难免,这关键要看自己的态度和功夫,取舍之间,高下立见。“二曰主敬则身强”。这句话说的是“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功夫也。”按现在的话说就是神情端庄,仪表整洁,对他人他物要恭敬,不能傲慢无礼。做人应当“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如此习惯成自然,久而久之就有了清明的心地,不俗的外貌,这对于自己对于他人他物都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三曰求仁则人悦”。严格自己,宽容他人,慈善为怀,积极向上,快乐自己,愉悦他人。不仅自己要有向善为仁的情怀,还要尽可能地影响他人以仁善为本,和睦共处,共同营造人人心静,不为外物所惑的人文环境,最终产达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外物的和谐。“四曰习劳则神钦。”意思是说人生来就有好逸恶劳的弱点,如果放任自流,不加自律,就会一事无成。如果能明白这个道理,从各个环节努力克服好逸恶劳的毛病,不断修炼自己,进而达到勤俭精进的自然状态,大丈夫立于天地间的人生目标就不难实现。所谓“极俭以奉身,极勤以救民”说的就是修身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必然过程,它的终极结果是能够自如地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入世境界。
从儒家整体思想而论,曾国藩的这些话似乎没有什么新意,但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一贯的,而且悟到做到了相当高的境界,就身体力行而言,他既不愧于先人,更无愧于来者,除去镇压太平天国的政治因素外,他的确是中国封建传统的精神偶像,为人楷模,还是担当得起的。作为能臣,作为父亲,作为兄长,他都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曾国藩的确是个厉害人物,他的厉害源于他对传统文化的载负,源于他的执着,源于他对他所信服的思想体系的穿透,源于他殉道般的身体力行。他给后世留下的堪称洋洋大观的符号,无疑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一个人,虽然我们反感于来自方方面面的过誉之词,但我们依然不能用所谓“对立的阶级”来否定不当否定的东西。文化遗产就应当从文化的角度去解读,肯定或否定都不能用非文化的标准去评判,不然,浅薄和误会了历史的肯定是我们自己。“革命”的思维惯性和因改朝换代频繁而割裂历史的习惯是到反省和痛定思痛的时候了,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我们已背上了这样的负荷,下一个传统否定上一个传统的做法和习惯已让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倘若我们仍继续在自以为是的圈子中舞蹈,断送固有文化的不是别人,肯定是我们自己。
从文化角度看一个文化人,看到的多是可爱。在这个意义上说,清廷对他的评价“学有本源,器成大远,忠诚体国,节劲凌霜。”还是有道理的。对历史人物标签贴的太多就复杂了,也失真了。
七
布哈林的绝笔信正如他的存在一样——阳光下一尊有些奇特的碑,这碑的里面有很多难解之谜。在这个意义上说,布哈林的碑便有了阴阳两面,阳面是他说清了他的死,他自己的集团和领袖为什么要杀他;阴面是这个集团这个领袖为什么要杀自己的功臣,因为布哈林并没有“谋逆篡位”,更没有取而代之的想法和作为。仅仅因为思想,仅仅因为忠诚于党的事业,布哈林及其那些元帅们就必须为那部庞大的机器作出牺牲,献出生命并背上恶名。这真是一个既特别残酷又特别有趣的现象,也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些鲜活的祭品,这万恶的机器才在血染的历史中被打开,历史的威力才把这机器拆卸下来,让那些零碎大白于天下。
要知道这机器的历害,还是看一看它的受害人在同一时期说出的截然相反的话。法庭上的布哈林是这样说的:“我不仅是反革命的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而且还是反革命领导人之一……因此,我不指望得到宽大……斯大林同志,他是世界的希望,他是新世界的缔造者。斯大林的英明领导,已经深入到全国每个人的心中……”我们可能会有些奇怪,和斯大林已成了生死冤家对头的布哈林不可能是这样的软骨头,难道他还奢望斯大林给他一条生路吗?布哈林比谁都清楚,即使他怎么的卑躬屈膝也是没有用的,他注定是这部机器粉碎的对象。但他为什么又要说出连自己都肉麻的话呢?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必须示弱,用示弱来满足对方消灭欲,让对方更加高大,更加孔武有力,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保全自己妻儿的性命,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疑也是极其痛苦的。布哈林的此等做法与我们的大臣被皇上赐死还要“谢主龙恩”一样,都是逼迫的。因为这机器是可以粉碎一切的,反抗与妥协结果都是一样,与其连累家人,倒不如图刽子手高兴。
真实的布哈林直到生命的最后也没有失去理性,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绝笔信》里他这样写道:“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党员变为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么这些机构也会立即找出证据来。”可见理性的布哈林并没有在精神上屈服,坚持真理的信念也从来没有动摇过。他要给世界留下他真诚的一面,因为他相信,虽然“历史上常有可怕的错误,但真理总有一天会恢复的”。这信仰、这真理绝对不是集团的、主义的,而是人的,大写的有尊严的人的。
布哈林只是苏联这部机器在运转过程中被粉碎的一员,谁让他赶上了呢?有数据可以表明这部机器真是历害了得,从1933年到1937年间,苏共党员(含预备党员)就由350万降到200万以下,1934年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委员中,被逮捕和处决的就有98人,1966名代表中,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而遭被捕的高达1108人。我们不禁要问这苏共集团到底在干什么?国家机器难道就是这样运转的吗?斯大林到底怎么了,这个党到底怎么了?
邪恶与正善,人性与他性,神圣的旗帜下面怎么会有如此残暴的行径?!这权力果真就是如此万恶吗?这些问题一时还真是说它不清。但从法国人路易斯·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一书中可能会找到一些答案,他说:“政治会败会人的良知,政治必须对下列危害极大的格言给人类带来的恶果负责,它们是:‘强权大于公理’,‘目的证明手段正确’,‘公共安全是最高的法律’。”如果疏于追究,那人还是人吗?政治还是政治吗?
但,不管怎么说,人是大于一切的!
八
一本《名人的遗书》把人读得天昏地暗,感觉深处总有一种在星空中遨游、在黑洞中飞行的眩晕,这些“与神对接”的符号直把人引向一方肃静而灿烂的星空,用“很有意义”来形容自我的体验还显得太过平实,不够完全。因为你面对的每一个人或静得博大、或动得大气飞扬,那些曾经激越慷慨或淡出俗场的生命,他们穿透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更为凝重而真实的价值,绵长或短促,啰嗦或简捷都有生命的体温散发着人的亲切。爱或者恨,奋笔击书或娓娓道来,生命流淌的痕迹清晰可见,其痕其迹划出了人生最美的弧线,这才是人生最壮丽的诗篇。更是那些虚假文化“做作”不出的,也正因为如此,那些俗世中的光环怎抵得上一声生命的浩叹!那些虚幻的桂冠又怎能和这些“善言”相提并论?!
感动的确是一个伤口,绝响给人的感动也许是永生的,这不仅仅是出于对逝者的哀怜,更多的是出于对生命的敬畏,那些丰盈的灵匆匆走过既往的时空,能够隐约感到的是历史的重负怎么能这么无情地辗过他们,超负荷密集地辗过他们,叠加的风云际会不仅压扁了历史,也吞噬了这些原本硕壮的英魂,这难道还不足以唤醒我们对历史的责任?因为我们也将成为历史,未来如何书写,关键还在今天。对英烈而言,不管他们的信仰如何,也不管他(她)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绝响,他们最后的心理历程虽然我们无法全部窥究,但站在是人不是神的角度来仰视这些人间豪杰,即或只是名流大家,我们也不可能是无动于衷的。我们惊异于那些既特别热爱生命又能对生命诀绝的人,仅用一个义士的名号是难以囊括其精神和思想内涵的,即便是历史的误会者,也可以看出他绵绵不绝的情思是如何抽尽的。而这样的过程正是生命备受煎熬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哪怕只是一点点微响,也能聚合为生命的最强音!
毋庸讳言,人在本质上都是惧怕死亡的。周作人在《死亡默想》中说世人怕死的原因大抵有三,一怕苦痛,二是不舍,三是顾虑亲人。但这些发出了生命绝响的人难道就没有这些顾虑,回答是肯定的。林觉民的抉择就很好地说明了他是有顾虑的,也是不舍的,但大义使然,历史要他献出生命,他就不能不舍,这才是绝响的价值,这才是生命更深层的意义所在,常人自是难以企及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时代都要有甘愿牺牲的人来点亮黑暗的夜空,在寂寂的大地上产生一些声响,用此来证明我之在、我们之在。有一点光亮和声响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在喧嚣的时代,不去制造噪音,能有一份宁静自然是好,这于己于社会都算是一种反叛,自然也是一种奉献。当然,一种太过强势的单音倘若是铺天盖地而又经久不衰,那么这个时代需要的就不是宁静了,她需要的是另类的声响,如此,噪音才可能逐步变为音乐。
这依然是从所谓的“道义”上说的。
从另外的角度上说,我更倾向于清静,对外部的所求无多,只要能够听到音乐就行;对自己更无奢望,能够宁静地生活,并成为常态,愚愿足矣!
在本文的最后,我仅以罗素的话来自勉——“每一个个人的存在,应该像一条河——开始时小,夹在狭窄的两岸之间,热情地奔腾澎湃,穿过礁石,翻过瀑布,渐渐地两岸退远了,河面变得宽广了,小流也较为平静了,终于,汇入了大海,与大地浑然一体,毫无痛苦的失去了个人的存在。一个人到了老年,如果能以这样的态度对待生命,就不会因怕死而感到痛苦,因为他所关心的事仍在继续下去。”
罗素的话可能与绝响的主旨相悖,但放到一个更大的参照系里,我们不都是一滴水么?!
生与死都有凝重而博大的内涵,为感动而写了几段浅陋的文字,但仍有言犹未尽之憾,怎奈话题太大,又感功力不济,难以敞开更多的秘密。只是有入思的过程,怕它稍即逝,姑枉录之。真是一滴水中的太阳,幸而照上了。
| 寒江雪 评论 (评论时间2010-10-03 00:58:30) | ||
| 黄振宙此文甚棒,令人百读不厌也! | ||

诗赋绽芳蕊 今来觅知音
版权所有:诗赋网 Copyright 2008-2016 zgshifu.com All Rights Reserved 辽ICP备18006388号
诗赋杂志投稿邮箱:sunwulang@163.com
联系人:轻盈 QQ:418193847、1969288009、466968777 QQ群号(点击链接) 电话:15609834167 E-mail:sttsty@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