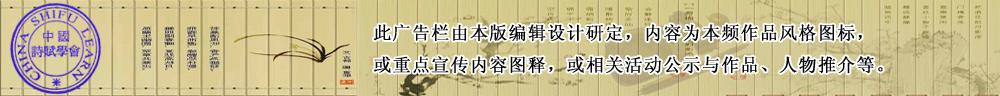
- 高原之魂 ——王芳散... [雨晴]
- 学诗之法... [青青子佩]
- 杂谈... [初生牛犊]
- 心底飞歌 ——诗人王跃... [雨晴]
- 实践确实是检验真理的唯... [江湖夜雨]
- 靡靡相思苦,阵阵刀割痛... [翰林院士]
- 《诗论》修改稿... [崔思军]
- 关于《临洞庭上张丞相》... [秋水孤帆]
- 学格律诗28问答... [秋水孤帆]
- 《赋写风华》贺序... [诗赋家王]
- 中国历史上十大骈文高手... [周晓明]
- 诗歌概论... [覃应海]
- 艺术含蓄学(全本)... [郭有生]
- 古代离情诗诗译书画意境... [王铁&n]
- 怎样写七言绝句... [风霜雪雨]
- 生命的珍果 思想的明珠... [晓雪(著]
- 平水韵表中没收入的汉字... [淘淘一笑]
- 艺术含蓄学... [郭有生]
- 扬东北诗风,创“黑土”... [程奎]
- 《大家一起来写赋》... [石涵]
文学到底是什么?似乎很难界定。一方面,文学的创作者自身置身于现实生活的环境中,他会受到现实渗透性的影响,他的作品,也就不可能完全超越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与时代的范围,所以,文学是现实的反映与产物。但另一方面,文学作为语言表达的工具,具有它自身的特性,是一门具有独立自足性的艺术。它要求作者具有超越性的主体意识,而不迎合世俗化的潮流与口味,强调作者自身的独立思索与自由创造。如果一个作者不能拒绝外界的“同化”,不能拒绝大众化庸俗趣味的媚惑,不能坚守自己的内心,往往就会使作品成为现实的附庸、主义的奴隶或政治的利益,从根本上丧失文学创造的艺术生命,使文学自身失去存在的意义。前者一般强调文学要为现实服务,热烈地拥抱现实的是非,强调文学的经世致用与功利性;后者一般强调对现实冷静的观照与审美创造,强调文学对现实泥沼的超越性,既超越政治的局限,也超越是非伦理的判断,不是反映什么,证明什么,传达什么,而是让大千世界和人类的生存处境尽可能真实地呈现在作品本身中,让读者自身去参与性地发掘、审美和品读。
文学中的这两种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呈现了“为革命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的两种风貌。而我发现,在郭沫若与徐志摩的身上,最突出地体现了这两种文学风貌之间的对立与分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核心理念,是“人----个体意识”的觉醒,强调作为个体的人自身所应具有的自由、尊严与独立的价值。这是继晚清和辛亥革命以来“民族----国家意识”觉醒之后的又一大思想裂变,具有极为重要的启蒙意义。在“人-----个体意识”觉醒的启示下,整个五四文坛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创作局面。郭沫若与他所从属的创造社,也从最开始就打出了“为自我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旗帜。郭沫若以其《女神》诗集登上文坛,其诗集中的《凤凰涅槃》与《天狗》等诗,于大震撼大咆哮的雄奇豪放中,追求和渲染的,正是一种冲决一切的极度的个性解放与自我意识的觉醒,体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所以郭沫若的诗在当时造成了普遍的影响。然而,仅仅过了几年,这位当时最具个性特色,热衷于“为艺术而艺术”的诗人,却在文学立场上来了一个大转变。这种变化可以参看他1925年11月底的《文艺论集》序:“我的思想,我的生活,我的作风,在最近一两年内可以说是完全变了。我以前是尊重个性、信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之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人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免有几分虚妄。”这就是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阶级意识”的觉醒,取代了他最初以“人----个体意识”觉醒为创造主体的文学态度。本来,如何使曾在“人----个体意识”觉醒下的深层审美心理和审美习惯,在新的革命时期完成新的转型,即完成现实与艺术在文学中的统一,是文坛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学课题。但是,由于阶级革命与抗战等迫切的现实情势,往往使人们来不及深刻地思索,也就造成了艺术表现与政治内容的严重不平衡,造成了文学艺术美的完全失落,使文学沦为一种功利化概念化的粗制滥造式的写作,沦为现实政治与革命的工具。具体参看郭沫若的诗歌创作,早期充满活力的个人风格逐渐消失,在公式化与概念化的革命呐喊与政治说教中埋葬了“真我”。这种趋势,愈到后来愈趋明显。据统计,从1949年到1977年28年间,郭沫若共写了新、旧体诗1000多首,可谓诗情澎湃,一路高产。但这些诗歌大多是对革命的顶礼膜拜与高度赞扬,基本上政治需要什么,他就做什么样的诗,例如,陪毛泽东登天安门,他写诗;为了大炼钢的壮举,他写诗;为大跃进的伟大成就,他写诗;为了接班人的不朽形象,他写诗;为了接班人的自我爆炸,他写诗······在对现实政治与权利的完全屈从中,体现的是人的主体性丧失的奴颜媚骨,例如,他在1976年写下了讴歌嚣张一时的四人帮的《水调歌头·四海通知遍》:“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到刘和林,十载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情。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然而,仅仅过了五个月,四人帮被捕,同一个郭沫若又写下同一词牌名的《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纂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满口陈词滥调的曲意逢迎与随机应变,完全成了政治的留声机与传话筒,毫无艺术可言。郭沫若的悲剧现象的教训是深刻的,体现了“阶级意识”对“人-----个体意识”的绝对压制,必然造成的以集体经验语言(政治语言)取代个性经验语言(文学语言)的文学创作局限。这也是大陆文坛六、七十年代普遍的教训。
而在徐志摩的身上,我们则看到了一种自始自终“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倾向的创造。他的诗空灵飘逸,独抒性灵,几乎新诗史上无与伦比,集中体现了一种个性解放与追求性灵自由的美学范畴,实际上也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个体意识”觉醒思潮合拍同奏的产物。当然,徐志摩置身于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不可能不受到现实的干扰。他的特点是在现实的高度打压下,始终不曾改变他“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理想,他的文学创作,也就不可避免地抹上了一种浪漫主义的悲剧色彩。在《猛虎集·序文》里,他有一段自白:“你们也不用提醒我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诉我这遍地的灾荒,与现有的以及在隐伏中的更大的变乱,不用向我说正今天就有千万人在大水里和身子浸着,或是有千千万人在极度的饥饿中叫救命;也不用劝告我说几行有韵或无韵的诗句是救不活半条人命的;更不用指点我说我的思想是落伍或是我的韵脚是根据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的……,这些,还有别的很多,我知道,我全知道;你们一说到只是叫我难受又难受。我再没有别的话说,我只要你们记得有一种天教歌唱的鸟不到呕血不住口,它的歌里有它独自知道的别一个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独自知道的悲哀与伤痛的鲜明;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徐志摩这样出于对文学艺术的忠诚是可敬的。他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忠诚理念因为坚持了自我,总是能够在作品中主观能动性地呈现瞬间的自由体验与审美情趣,例如他的《再别康桥》、《偶然》、《沙扬娜拉》等,都是具有永久艺术价值的传世名篇 。 但另一方面,个体躲在象牙塔中,“为艺术而艺术”,并非不能感受到外界重压(革命的道义与社会的伦理等意识形态)的逼入,这也会导致文学主体性的迷惘与丧失。例如徐志摩在《猛虎集·序文》谈到的自己后期的写作状况:“尤其是最近几年有时候自己想着了都害怕:日子悠悠的过去内心竟可以一无消息,不透一点亮,不见丝纹的动。我常常疑心这一次是真的干了完了的。········最近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茅盾在《徐志摩论》中分析得好:“因为他对于社会的大变动抱着不可解的怀疑,而又因为他是时时刻刻不肯让绝望的重量压住他的呼吸,他要和悲观的怀疑挣扎,而且他又再不肯像最早写诗那时候把半成熟未成熟的意念都‘托付腕底胡乱给爬疏了去’,于是他只有‘沉默’的一道了!这是一位作家和社会生活不调和的时候常有的现象。”------说到底,一味地“为艺术而艺术”,会产生对现实生活的隔膜,让自我失去对现实的辨别,使他陷入“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的傍徨和迷惘,从而进一步扼杀其艺术创造的活力。
这里需要附带指出的是,徐志摩后期对自己的思想是有所觉醒的,这依然可以从他的《猛虎集·序文》里看出来:“继续的行动与北京的风光却又在无意中摇活了我久蛰的性灵。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嫩芽的青紫,劳苦社会的光与影,悲欢的图案,一切的动,一切的静,重复在我的眼前展开,有声色与有情感的世界重复为我存在;这仿佛是为了要挽救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那在帷幕中隐藏着的神通又在那里栩栩的生动:显示它的博大与精微,要他认清方向,再别错走了路。 ”------“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就是他最好的自我批判。这种自我批判是建立在对“劳苦社会”等现实的关注的基础上的,也就格外具有警醒的深度。这就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他执着追求真理和关注黑暗现实的理性与良知,终会使他从过去陷入“单纯信仰”(主要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理想)的“怀疑的颓废”的局限里蜕变出来,从单纯的“为艺术而艺术”慢慢地转变为兼顾“为现实而艺术”,这种变化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可以慢慢实现的。可惜的是,渴求“复活”的他,却意外地早逝,一切转变的可能,成为了永远的泡影。
既让艺术时时拉回沉沦于现实世界中的主体,又不让现实戕害艺术(如郭沫若);既让艺术以良知关照人类的现实性活动,又不让艺术过度漂浮于现实之上(如徐志摩);既在现实中进取,又在艺术中提升,以实现艺术和现实的统一,这其中有没有一种折中的办法?这里,我不妨借助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的著名命题来试图作出解答:存在先于本质而出现,先有生命本体的存在,而后才会派生意义。文学艺术也一样,从人类诞生起,文学艺术最基本的立足点首先是心灵、情感、审美与生命的需求,然后才是生存环境中政治、道德、功利等经世致用的实用需求,所以,因该首先回归文学本身最基本的出发点,“为艺术而艺术”,然后再考虑它在现实中可能派生的意义。如果采用“本质先于存在”的认识,以先验动机让主题先行,例如“为革命而艺术”,便会让主题充斥其中而导致艺术的丧失。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郭沫若在转变为革命而艺术的同时,能让“本质”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自我“存在”的意义;如果徐志摩在艺术的象牙塔中“为艺术而艺术”的同时,能让自我的“存在”提醒自己不要过于忽视现实的“本质”,那么,他们的文学作品,就会比今天所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已经不凡的实绩,要伟大得多。
这种教训,并不限于他们二人。在文学艺术与现实没有取得统一而严重偏颇的现代文坛,这种批评的视角,普遍适用。

诗赋绽芳蕊 今来觅知音
版权所有:诗赋网 Copyright 2008-2016 zgshifu.com All Rights Reserved 辽ICP备18006388号
诗赋杂志投稿邮箱:sunwulang@163.com
联系人:轻盈 QQ:418193847、1969288009、466968777 QQ群号(点击链接) 电话:15609834167 E-mail:sttsty@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