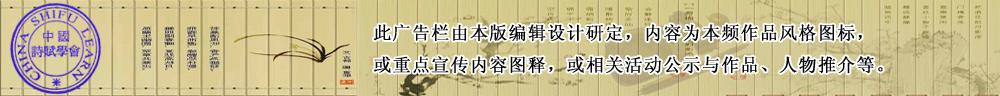
- 踏访红崖,寻访掉龙湾... [绿染秋情]
- 让我好好陪着你... [史春培]
- 晚安,旧时光... [惜若]
- 紫玉生烟... [莫小仙]
- 再梳妆... [莫小仙]
- 闲话大维... [史春培]
- 蓦然回首间... [云木欣欣]
- 明朝一哥王阳明(续)... [蓝色小妖]
- 年少不识爱滋味... [徐姜清]
- 浅析甲午战争期间一封日... [云木欣欣]
- 《白鹿原》读书笔记--... [谭长征]
- 《白鹿原》读书笔记--... [谭长征]
- 广西浦北县恢复建县45... [韦志远]
- 《白鹿原》读书笔记--... [谭长征]
- 人性的丑陋没有底线... [醉玉如雪]
- 《白鹿原》读书笔记--... [谭长征]
- 戏剧人生如梦诗(2)... [韦志远]
- 圆锁庆典家长祝词... [气自华]
- 月窗探骊---文集... [郭有生]
- 试拟长篇小说《平凡的世... [谭长征]
童年的记忆
随着年龄的增长,沉淀在童年记忆里的往事,又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双双慈祥的面孔、可爱的笑脸,那一对对虚伪凶狠的目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永远也忘不了,是他们使我过早地失去了童年的欢笑,也是他们使我过早地懂得了生活的艰辛和世态的炎凉。
我记得,文革开始的那年,我才八岁。有一天夜里,我们刚准备睡觉,刘街长带着三四个红卫兵来我家通知说:要我们三天之内离开县城,到我父亲所在公社的农村居住,否则,将要戴高帽游街和封门。白天,我带妹妹到街上玩时,看到过有几个人戴着用纸扎成很高的帽子,名字写在帽子上并打个大大的红叉,脸上画着花脸,有个女的还剃了个半边头,他们脖子上也都挂着很重的大牌子。一路上,他们谁走的慢了,还要挨戴红袖章人的拳打脚踢。我看到站在刘街长身后两个戴红袖章的人,不就是白天打人的那两个家伙吗?吓得我和妹妹直往母亲的身后躲。送走他们,母亲就带着我到对门的单位上给远在几十公里之外的父亲打电话,要父亲马上回来安排搬家的事。
第二天中午,父亲回来了。在他的身后跟着几个拉板车的农民,母亲说,父亲接到电话后一夜都没有睡觉,那几个拉板车的人,就是我们要去那个村的。那天傍晚,当母亲带着我们姊妹四个和奶奶出现在村口的时候,我们两架子车的全部家当,被村里二十几个男人们,一涌而上,三下五去二的几下子,就把我们家的东西搬进了生产队现腾出来的仓库里,这就是我们的新家。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收拾一下,大娘大嫂们就把我们这家往屋里拉,那家往屋里拽的喊着说吃饭去。母亲说:担心受怕的日子总算结束了。
几天来,我们被东家喊西家叫的,整整地在村里的每一户都吃了一顿。比当时接待上级来生产队检查的干部吃的派饭还要隆重。我们的新家里真比过年还要热闹,这家给点米、给点面,那家给点大葱、青菜,还有人拿着鱼、肉、油之类的东西,来给我们攀亲戚。他们不管你认不认,那个亲热劲跟没有出五服似的。他们也不管你家里缺不缺这样东西,只要是他们家里有的,他们都要给你送一些,你想不要都不行。还有那个被村里人喊着叫“老干部”的贫农代表许国,非要说跟父亲是战友不可,父亲笑笑也就没有再说什么。其实,父亲是在50年春天复员到地方的,而许国是50年冬天朝鲜战争爆发后,才参军的。
在盖房时,许国不要我父亲管盖房子的事,他自己亲自带着村里的一帮年轻人到山里去放檩子、砍椽子,打泥墙,割山草。他对我的父亲说:别的你插不上手,你只要准备些烟酒就行了。烟酒,在今天说起来不算个什么,可在当时是计划经济,一切都是定量供应,烟酒都是凭票供应的紧缺东西。一户一个月凭票才半盒烟,一年才两斤散装的红薯干酒。那时候,你想弄点烟酒真比登天还难。他们知道,我父亲是公社卫生院的院长,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在不行了弄两瓶酒精总没有什么问题吧。当时有许多人弄不来酒,就到医院弄点酒精,按1:3的比例兑些凉开水,不也一样的喝嘛。父亲找到当时在公社供销社当革委会主任的战友,好说歹说才特批了五条烟,五十斤红薯干酒。当时流传的是:听诊器、方向盘、木什疙瘩、营业员是最吃香,也最有实权的职业。许国他们十几个参加盖房子的人,每个人不但吃喝了几天,还分到了一盒烟、两斤酒。把那些没有能够参加上盖房子的人羡慕个半死。最后,父亲又找人买了五盒烟、十斤酒,把那些没有参加盖房子的村里人,又叫到了一起吃喝了一顿。父亲在村里人的眼里,是最有本事的人。他们有什么事了,总喜欢去找我父亲,父亲又总是尽量的满足他们。许国总是一脸自豪和得意的在村民中说道:没有我战友办不成、摆不平的事。
或许是父亲的缘故吧,我们家也成了当时生产队里最热闹的去处之一,他们见了母亲总是大婶长大婶短的不停口。我母亲不但慈祥宽厚,还会打针,针灸,用缝纫机做衣服。况且,我们家,男人们来了有烟,女人来了有茶,可以说是常年不断。就连我们姊妹几个在村里一下子也都成了能人,村里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时,非要让我哥哥当宣传队的队长和艺术编导,姐姐当节目主持人。其实,哥哥和姐姐他们当时也才十四、五岁,根本不懂得什么,无非是在城里长大的,胆大一点罢了。我和妹妹在村里也成了“孩子王”。小孩们打架吵嘴了非让我和妹妹给他们评评理,就连他们在家里不听话淘气了,他们家的大人也要找我和妹妹去管管他们的孩子。仿佛我和妹妹就是村里孩子心目中最有权威的“小国王”。
记得有一次,我带着村里一帮小伙伴在池塘边玩,大家找一些石头、瓦片玩起了撇撇游,手里玩着,嘴里还不停地喊着:撇撇游、撇撇游,一下打到堰那头。谁知道,我玩的那一个撇撇游,燕子似的在池塘中溅起了一串长长的水花之后,竟飞到了对面的人群里,把队长的儿子,也就是贫农代表许国的侄子许耀给砸哭了。我跑过去一看,他的头竟被我石片给打破了,他一边哭着一边捂着头,弄得他满脸都是血。这时,正好许国从这里经过,看到他侄子的头直流血,就大声的吼骂起来,我当时就吓的要哭,当他知道是我把他侄子的头打出血的情况之后,他不但没有打我,也没有再骂了,而是笑着对我说:没有事、没有事,洗洗一包就好了。他转过身对他的儿子就是一脚,嘴里还骂着:小兔崽子,还不快领你哥哥去包包……。
这件事,虽说过去了三十多年,可我一直到现在也忘不了。要是换了别的小孩如何,他们不挨打,肯定也要被臭骂一顿的。我知道,我没有被许国他们打,也没有被他们着责骂,是因为我父亲的缘故。那事,要是出在父亲去世之后,我是要倒大霉的,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第二年冬天,父亲所在公社的税务所市场管理员小王,在看菜地的窝棚中莫名其妙的死去,当时的公检法都已经砸烂了,县里只来了一个革委会的人和公安局里一个管户籍的民警。无奈,他们硬是拉上父亲去给小王验尸。父亲根据小王脖子上的掐痕和他身上有青紫块的情况看,认为不是正常死亡。父亲说:我昨天还看到小王,他健壮的象一头牛似的,一个才二十多岁的年青人,怎么会这么快就莫名其妙的死去。父亲知道,小王他坚持原则,工作认真负责,在平常的工作中肯定得罪过一些人,况且,他还是五二三群众组织的一个头头。父亲不顾在场还有二七联总人员,那一双双冷冷目光下的一再追问是不是正常死亡。还是根据实际情况,坚持写下了“非正常死亡”的验尸报告,并在验尸人栏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也正是这一个“非”字,给我们带来了一连串的灾难。先是哥哥和姐姐在宣传队里的“位子”被生产队莫名其妙的给撤掉了,接下来是我和妹妹在村里孩子们心中的“王位”,也被推翻了。父亲也在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被害死在出诊回来的路上。后来听临村的一个老师说:他曾听到许国在酒后说过他知道张院长是怎么死的。就说他说的是酒话吧,最起码他也知道一些其中的内情。他不但是当地二七联总分部的一个小头目;他也曾几次让别人以出诊的名义把我父亲“请”到一个地方,专门问税务所市场管理员小王到底是怎么死的。他们要父亲说小王是“正常死亡”,遭到了父亲的严词拒绝。
父亲去世之后,全家生活的重担一子都压在了我母亲的肩上。那时候,我们上有快八十岁的奶奶,下有我们姊妹四个,一家六口人,就母亲一个人在生产队挣工分。我们每年既得向生产队交两百多块钱的缺粮款,还得到集市上去买两百多块钱的粮食。母亲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还要在家里点着煤油灯用缝纫机给别人做衣服挣工分。还有我们四个上学的费用,日常的花销,全家靠父亲那一个月每人四元钱的抚恤金是远远不够的。母亲喂猪、养鸡,没日没夜地在生产队里劳动,在家里,还要用缝纫机给别人做衣服,好挣一点工分或是零花钱。还要抽时间洗衣、做饭、种菜园,半菜半粮的凑合着过。日子苦的真是没法说。
那年,村里人都到三十多里外的吴城去买猪,说那里的猪便宜,母亲说也让我跟许国他们一起去买一头回来。说起来,我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懂个什么买猪呀,不就是他们说那头好,给买一头,我好赶回来。可那时候是计划经济,食品站的生猪计划没有完成,是不能够随便买卖的。更别说我们这是跨县的买卖,一但被他们食品站的人发现了,不是被没收,就是被按他们食品站里收猪时的最低等级的价格买给他们。他们大人们有经验,也会买,他们买一头就从集市中把猪赶出来,藏在一个地方。等他们的猪都买好藏起来之后,已经快中午了,也没有什么象样的好猪了,最后,他们给我买了一头跟野猪似的红毛猪。还没有等我把猪赶出集市,就被食品站的人发现给没收了,许国他们看事不好,赶着他们的猪就走了。无奈,我只好跟着来到了食品站。许国他们到家说,看来我们的猪十有八九是没有希望了。母亲急忙赶到吴城,找人打听拦猪的人到底是谁,许多人都说马龙不好说话,在和别人的闲谈中,有人说起了他是固县人,并说起了他的家事。我一听马上接了一句,是不是住在西关马豹家附近;那人忙说,他就是马豹的大哥。马豹和我哥哥是同学,我们又来到食品站,找到马龙把马豹一说;他说,你们家的事,他也听说过,上午你们乍不早说呢。现在天还亮着,你们把猪再从猪圈里赶出来也不好看,等一会再说吧。你们从中午到现在还没有吃饭吧,走先吃饭去,停会我送你们走。那晚,我们赶着猪回到家里已经快半夜了。
第二天,当村里的人们看到我们竟把猪给赶了回来时,他们都感到不可思议。后来听说,他们当时给我买的是一头家猪和野猪的杂交猪,虽说不好看,可它泼皮,长的快。那年,他们喂的猪在发猪瘟时都死了,这头猪倒是给我们卖了一个大价钱。
父亲在世时,我们家里就是有,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的人,也还总是要想法的给我们送一些吃的、用的。等到父亲去世了,当我们真正遇到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去找他们帮忙,向他们借点钱、借点粮什么的。你看他们谁个躲的远,生怕你沾上了他。那年,我和姐姐去给住在城里的大姨拜年,大姨说今年没有买鱼了、没有买鸡了等等。当大姨去做饭的时候,我和姐姐在她房屋里面的柜子里看到了好几条油炸鱼和三个煮熟的鸡。从那以后,我们姊妹四个谁也不愿意再到大姨那里去了。回想起那年月,我心中现在还有点隐隐的做痛。说起来,你们现在可能还有点不相信,当时才九岁的我,为了能够吃上一顿大米饭,竟哭闹着也要跟村里的大人们一起上山去拾柴,来回四五十里的山路,别说是担点柴,就是空手也够一个十来岁孩子跑的了。
母亲是一个好强的人,在生产队里干活时,也是有说有笑的,可在没有人的时候,我看到母亲曾好多次的在偷偷的流泪。我忘不了,母亲在吃饭的时候,总是把稠的好吃的分给我们,说我们都是在长身体的时候,营养要跟得上。可她自己却喝的几乎是能够照见人影的稀汤,还要咬着牙,坚持到队里干重体力的活,为的是能够多挣一点工分,少掏一点缺粮的钱。日子之苦,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时,也曾有不少好心人劝母亲说:“别让你的孩子们上学了,回来给生产队放个牛,也能够挣几分,少掏点钱,还能够多分一点粮食。”母亲总是说:“孩子们的父亲死的早,他们也够可怜的,再说了,以后还要实行机械化,没有文化不行。现在,我们的日子是苦一些,我们咬咬牙,还可以坚持,没有钱,我们还可以想法的去借,等到孩子们长大了,没有文化知道艰难时,文化可就借不来了……。”
现在,我们姊妹四个,最低的也是个高中毕业,并都参加了工作。村庄上的人都佩服母亲有眼光,说母亲在解放前上过两年师范,看问题就是不一样。
那时候,一个学生能不能够上学,并不是看你的学习成绩如何,关键是看村里贫农代表的推荐,大队的政审,学校的意见,三方有一方不同意,你就上不了。
听母亲说,我们刚来的时候,有几个生产队都争着要我们在他们村上落户。我想,主要是父亲的缘故。可父亲去世后,情况也就大不一样了。和我哥哥一起上学的是贫农代表许国的大侄子,当年推荐上高中的标准是二比一,我们村只分给了一个的名额。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天,在大队的推荐会上,由于贫农代表许国的大侄子在学校里也是一个出了名的人。学校的代表坚持不要他,学校的代表说我哥哥学习好,想让我哥哥上。可村贫农代表许国口气非常强硬地说:要不要就是这一个。根本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最后,双方相持不下,这一个名额也作废了。许国家里的人在村里放出了话说:我们贫下中农家的孩子上不了学,他地主家的孩子还想上学?别想。开批斗会时,不叫他们家的人“台”上陪斗,已是给了他们家很大的面子了……。后来,虽说我们姊妹四个也都上了高中,可那都是亲戚、父亲的朋友和老师们从中帮的忙。
我十岁那年的冬天,天出奇的冷,池塘里的冰结的有一尺多厚。那天,我放学后,踏着厚厚的积雪艰难地往家里赶去,怒吼的东北风携着鹅毛似的雪片,一阵阵地迎面扑来,脸上顿时觉得刀子割一样的疼痛。这时的我,多么想快点回到家里,坐在火边烤一烤。可是,我知道,这大雪又整整的下了五天了。家里做饭用的柴火都有点紧张,还那有柴火烤火,就连我们做饭用的柴火,也一直都是我们姊妹几个利用中午和晚上放学后的时间,我们分别沿着别人上山的几条路去拾柴。有时,我们要一下子沿路跑上七八里才能够拾上一筐柴。现在,眼看着我们的柴火垛是越来越小,雪还没有要停的迹象。我们那八十来岁的老奶奶冷的实在受不了了,偎在被窝里也不叫生火;母亲忙着用缝纫机给别人做过年的新衣服,做一条裤子4角钱,做一个上衣7角钱。母亲冷的没有办法了,她就在她的腿下放上一个火烙,有时在火烙里面按上一些草末子,弄得满屋都是烟。那时,木炭虽说只才七八分钱一斤,可我们舍不得,也买不起。那天,我到家后,来不及拍一拍身上的雪,放下书包,掂上斧头,捞了个筐就出去了。我想起来了,路边有一棵碗口粗的杨树,已经死了一年多了,我何不把它给砍了拉回来,也够烧上两天了。我刚刚把树砍倒,就被贫农代表许国看见了,他跑过来一把拧着我的耳朵,给了我两脚,嘴里还一个劲的骂到:你个小兔崽子,你敢砍树毁林,走,见李拐子去。他一边拉着我走,一边喊他的儿子把树给拉到他家里去了。李拐子是我们大队的护林员,二十多岁,脾气很坏,好认个死理,只要看到那个小孩动了他的树了,挨打挨骂是少不了的。就连大人们也不敢轻易的去摸他的树招惹他。我今天落在他的手里,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还没有进院,许国就大声地喊道:“拐子,快出来,我给你抓了一个偷树的贼……。”“谁呀,老干部。”我吓得不敢进院,直想往后跑,可许国一直在抓着我的衣服领子,我根本就没有跑的可能。许国把我往李怪子的面前一推,把我为什么要砍树的经过对李拐子说了一遍。然后,许国吹着口哨回家去了。李拐子把我拉进屋里,什么也没有说,他让我坐那先烤火,他却站起来不知道忙什么去了,我心里更加的害怕,难道他是在找打我的东西吗?我的眼泪一下流了出来,可又不敢哭出声来。他从屋里出来看到我的样子,笑着对我说:哭什么,走,我送你回家去。看来他是要当着我母亲的面来修理我了。正在做衣服的母亲看到我和李拐子一起回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起来打招呼。李拐子放下袋子,对我母亲说:大婶,你以后有什么难处了,尽管对我说了。这是一点炭,你们先烤着……。说罢,他头也不回的走了。据说,犯在李拐子手里,没有被他打骂的,我是唯一的一个人。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些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留下美好回忆的人们,虽说,我没有办法报答他们什么,可我心里,一直在默默地祝福他们——好人一生平安。还有那些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留下了深深创伤的人和事,我虽说不想记恨他们,找他们报复什么,也尽量的不去想他们,却还是难易忘却……。
作 者: 张克刚
作者单位:河南南阳油田钻井公司管子站
联系电话:13569229248
邮政编码:473132
电子邮箱:zkg1959@sina.com zkg8868@126.com
| 雨晴 评论 (评论时间2010-04-21 21:26:00) | ||
| 童年的经历、刻骨铭心的记忆。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灾难。欣赏作者的回忆录!问好! | ||

诗赋绽芳蕊 今来觅知音
版权所有:诗赋网 Copyright 2008-2016 zgshifu.com All Rights Reserved 辽ICP备18006388号
诗赋杂志投稿邮箱:sunwulang@163.com
联系人:轻盈 QQ:418193847、1969288009、466968777 QQ群号(点击链接) 电话:15609834167 E-mail:sttsty@sina.com



























